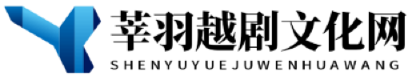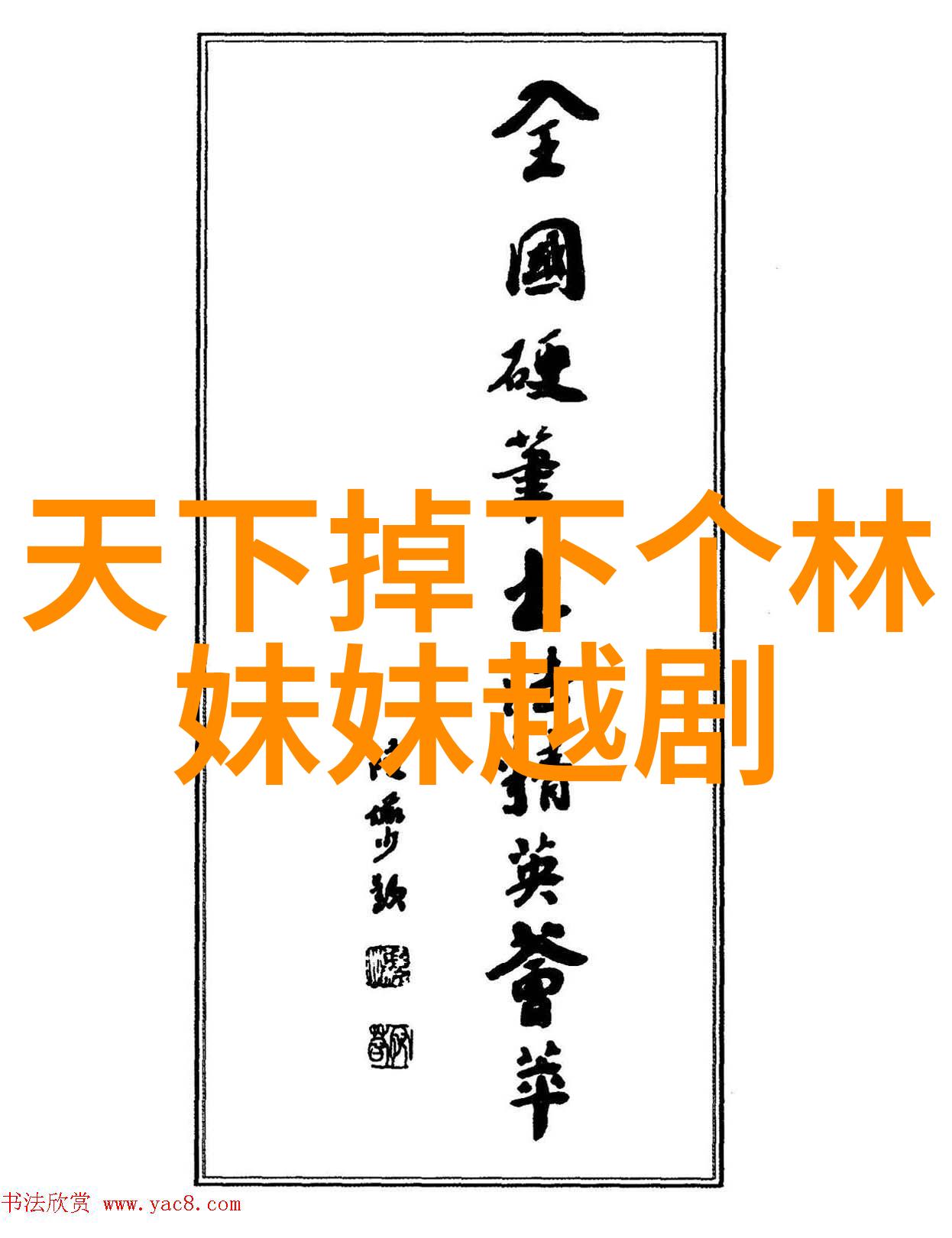《江南好人》:越剧剧种的“好人”还是“坏人” 厉震林《上海戏剧》2013年第5期 对于茅威涛和郭小男,我总是有所期待的。它基于两人对于越剧的使命感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越剧美学体系的改革精神,并将它扩展到整个戏曲领域的发展方向探索。艺术改革,必然是对原有戏曲文化生态的一种修正、创新和重立,故而也必然具有一种风险性,它涉及到细分观众的不同接受程度及其戏曲从业者的利益攸关和习惯惰性。它既需要天才,更是需要胆识,非常人所能承担,也非常人所能忍受之痛。 它需要一种大文化人的胸怀和智慧,有着改革目标的清晰设计以及精神立场。在我的隐约感觉中,茅威涛和郭小男似乎有着如此前行的身影,显得有点傲气,也有点孤独。 在观看《江南好人》之前,与郭小男匆匆见了一面。看完演出以后,想起郭小男的脸,近些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如同刚刚观看的戏,与若干年前的戏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它仍然是那么地充满力量感,包括人文的、美学的、艺术的。你可以不喜欢郭小男的戏,但你很难忘记那些颇有力度的角色性格、台词、形象设计以及舞台调度和造型。它必然与众不同,它必然精致到位,它必然哲学情怀。说是郭小男的戏没有什么变化,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变法”,“变法”是他的不变。它需要足够的韧性和耐性,以及足够的才气和才情,一定经历过太多的“变法”之痛,累并快乐着。 茅威涛、郭小男之所以选择改编这部被全世界无数演绎的名剧《四川好人》,应该是企图借助于充满悖论哲学意味的原著,进一步强化自己对于新越剧以及新戏曲的文化建构。近代以来,戏曲的文学功能逐渐被表演功能所取代,戏曲对于社会人生的宏观俯视以及整体阐述能力日渐衰弱,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一种表演的玩偶,一种歌舞升平,一种生活情调,一种附庸风雅,在人文精神上已无法与现实生活无缝对接。显然,茅威涛、郭小男不满足于多数戏曲作品题旨的二元逻辑,在现实远比艺术更为丰富多彩以及曲折深刻的情形下,希望建立多元逻辑甚至模糊逻辑结构,与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对话。因此,也就使戏曲具有了一种现代感,既是“仰望星空”,又是“脚踏实地”,也就是说,高可攀越哲学,低可接通地气,使人感觉到戏曲有可能成为人生哲学或者生活况味的启迪大书。茅威涛、郭小男选择了《四川好人》,也就是选择了戏曲艺术的一种方向。请看他们在改编的作品中,抬升了原著的悖论命题:原来善良与罪恶同在,为了行善,必须用罪恶保护;贫穷往往与懒惰、依赖有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无法承担重担的人,却承担了如此重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所谓洞察世界的神仙,也只是几个幼稚天真的糊涂虫,世上不存在真正的“救世主”。这些作为浓彩重墨高歌的戏曲题旨,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现状是多么地“隐喻”、“暗示”以及象征。从《四川好人》到《江南好人》,茅威涛、郭小男以自己的戏曲变革强力,血淋淋地介入了中国现实社会的精神阐述,也确立了自身作为戏曲文化人的现代品格以及思想者的魄力。 我在多种场合中,表述过当下文化的“精神地图”变迁,一是从精英知识分子时代到泛知识分子时代,从某种意义而言,知识分子时代已经结束,或者说已是全民知识分子时代,已不存在“文化启蒙”,而只能是“文化自觉”;二是“代沟”超过了“地沟”,互联网时代地理的“沟壑”出现了消弥的趋势,而“代际”的周转频率逐渐加快;三是从信息不对称到信息对称。在如此文化格局下,戏曲发展有着二种的途径以及方向,一是表演的精致化,达到一种美伦美奂的极致境界,使戏曲成为表演美学的样式载体,如同青春版《牡丹亭》;二是采取一种变革的文化立场,寻求与当下观众的新思想和新形式的契合点,只是这种契合点颇难以创造和确立。毫无疑问,茅威涛、郭小男采纳了后一种路线,他们希望自己的“蜕变”及其努力,使越剧能够与二十一世纪的观众“一见钟情”,探索越剧的E时代的文化图景。 因此,当他们选择了《四川好人》改编的悖论哲学主题时,不可能使用传统的舞台呈现形态进行表述,而同样采用了越剧变奏的现代感,个别桥段甚至出现了去越剧化的元素,使人感觉到是越剧但又越剧意味稀薄的意象。第一,是拼贴的表演“杂交”现象,一些非越剧艺术样式的表演成分融入其中,使越剧在一种当代社会的艺术“珂拉支”现象中,《江南好人》成为了一种越剧的边缘样式或者新样式;第二,唱腔的“杂交”以及新设计,甚至有现代流行歌曲融合其中,使越剧的“曲”味时尚化,也使演员表演的内心“底色”以及节奏发生了变化,舒缓的诗意表演有所淡化,而充满哲学对撞以及灵魂搏奕的表演形态得到强化;第三,是舞台调度的话剧化,前半部分的市井生活颇有浓郁的话剧修辞意味,非常流畅而又生活气息酽然,而且,营构了若干造型感很强的舞台表演画面。 从某种意义来说,《江南好人》难以说清是一部什么风格的戏曲作品,但是,各种风格又浑然天成地融入作品之中,这是茅威涛、郭小男过人的才气所在,证明他们有能力驾驭这样的“变法”作品。稍感遗憾的是,结尾处出现林黛和隋达“雌雄同体”的投影时,由于前面一直是两个演员扮演这两个“角色”,它在直观的表演形态上就削弱了主题的“复杂”深度。这自然是由于茅威涛是一个女“小生”演员,女性角色的林黛就由另外一个旦角女演员饰演。由于不是同一个演员表演“一体两身份”的主角,因此,演员也就难以清晰而准确地表达出主人公两种性别身份转换之间的微妙感情以及神态,导演在处理两种身份时,也使两种身份有着简单化甚至概念化的倾向。其实,演员表演的真正魅力正是出现了两种性别身份变化之中的人格“”状况。 中国社会处于二千年以来最大的转型时期,它也必然裹卷着文学艺术的巨大变化。如同当年北京都市娱乐经济的发展,使徽剧、汉剧逐渐融合演变成为京剧,目前有战略和胆略的戏曲改革家也企图使在农业经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戏曲艺术,如何适应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观众的新审美需求和情感图谱,并构建一种属于城市文明的新戏曲剧种。茅威涛、郭小男也在探索着二十一世纪越剧“升级”之路,《江南好人》是它的一个实体标本,甚至是在越剧基础上“蝶变”出一种新浙剧。自然,它有着两个很大的风险,一是因为新,一批老观众接受不了,离去了;二是因为新,一批新观众还不熟悉,不会来。如此左右失据的状况,并非不会遭遇。因此,《江南好人》对于越剧来说,如同剧中“好人”和“坏人”难以分辨一样,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是颇难分辨。《江南好人》的结尾处,林黛央求三位神仙不要将如此“大任”降于其身,似乎也是茅威涛、郭小男的“夫子自状”,改革的艰难一定也是“遍身伤痕”。不过,戏曲改革总是令人尊重的,不管它的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抱有宽容的文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