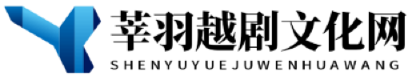佘惠民 早在男班艺人流动于浙江各地时,已从“东阳班”——婺剧移植出了《碧玉簪》。婺剧《碧玉簪》的基本剧情是:新婚夫妻王玉林、李秀英,因表兄顾文友以骗得的碧玉簪和假情书进行诬陷而失和,李被王长期。李不知内情,为求夫妻和好,百般忍让,最后竟被其父以“不贞”罪名一脚踢死。后查明,王玉林愧悔至极,碰阶而亡。顾文友则送官府问斩,成了所谓“三家绝”。移植后稍有不同的是,李秀英的性格更为委婉温顺(婺剧“三盖衣”中有李秀英在气愤之下举拳欲击王玉林的动作等),最后是郁郁病亡;顾文友则相思而殁。《碧》剧是封建礼教统治下的一出人间悲剧,但当时演出并不被观众所喜爱,艺人们自己也有不忍让善良的李秀英无辜被残害之感,时有改作之念。后艺人马潮水从书摊购得《李秀英宝卷》和《碧玉簪全传》,从传书中“对笔迹”的情节得到启发,决定将《碧》剧予以改编。他们以婺剧的情节作骨架,而对在李父赶至王家问罪一场中,当堂拆对笔迹,看出情节是假之后的情节,以玉簪被借未还为契机,作了大幅度改写:大白后,王玉林愧悔交集,发奋读书,得中状元,请来凤冠霞帔向李秀英赔礼认错,把“三家绝”改为“送凤冠”大团圆的结局。同时,他们又摘取卷书唱词加以修改运用,使原来的“路头戏”成为有了相当固定台词的“肉子戏”。改编后的《碧》剧,于1920年男班第三次进上海时在海宁路天宝里民兴茶园首次上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几乎场场客满。这是因为,当时“小歌班”在技艺上已有多方面改进,能为上海观众所接受。更由于正值“五四运动”之际,争取女权进一步兴起,《碧》剧以及相继上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内容上同情与讴歌女性,适应了潮流,故为观众所欢迎。“小歌班”也从此在上海站住了脚跟。以艺人自己的话说,《碧玉簪》是在上海立脚的第一本戏。第一次演出的阵容如下:李秀英——费彩堂,王玉林——张云标,李廷甫——马潮水,李夫人——金千法,婆婆——姚方松 改编后的《碧玉簪》虽然被讥笑为又是“中状元”、“大团圆”的“老套”,但它却成了越剧的重要保留剧目,常演不衰。农村妇女说:看《碧玉簪》是去哭一场的。明明自知去“哭一场”,她们还是久看不厌,这是因为《碧》剧为她们吐诉了久久郁积的怨愤,当最后看到王玉林手捧凤冠跪地求饶时,她们终于开怀畅笑了。 解放初,《碧》剧和其他许多传统剧目一样,因其“宣扬封建礼教”而不再出现在舞台。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千百年封建毒素熏染的头脑并未洗刷一净,家庭中的纠纷以及种种社会讥诮、诬蔑,仍然像一条黑色锁链缠绕着妇女的身心,无法挣脱。众多的见闻,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碧玉簪》,将这个以表现妇女遭受封建礼教残酷的剧目,予以修改演出是会有教益的。根据老艺人张云标的口述记录本,我作了改编。为了揭露封建罪恶,剧本让李秀英仅仅为了追求家庭和睦而遭受莫名的折磨,最终含冤而亡(实际上又回到“三家绝”老路子)。1952年由绍兴地委鲁迅越剧团演出于绍兴觉民舞台。但出人意料,演出效果奇差。不仅观众寻之怨怪愤懑,领导对如此改编也不予认可,演出仅一场即告终。然而,这个在苦难中的弱女子形象,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 1956年,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了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力进行各种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和改编工作,重又勾起我对《碧》剧的思念,也觉得必须对其重新认识;早先的《碧玉簪》固然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但前途昏暗无望,难怪观众、演员都为之不满。男班改编成大团圆结局,虽是“老套”,但一折“送凤冠”对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作了淋漓尽致的控诉和抨击,对妇女来说,是她们内心怨愤的申雪,也是对她们精神上的一种激励,显然具有积极意义。男班的这一改编是创造性的一着,功不可没。至于“中状元”、“大团圆”的结局,正是人们对善良的颂扬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同不少传统剧目与古典戏曲展现的团圆结尾一样,是一种可贵的乐观主义民族心理的反映,不能笼统否定。但原剧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顾文友见鬼魂“捉蜻蜓”等封建糟粕,当然是应该剔除的。基于以上认识,我对《碧》剧作了重新整理。除了去芜存菁和语言加工外,省略了顾文友一线,而在“回娘家”、“三盖衣”、“送凤冠”等重要场面作了更多的阐发。 整理后的《碧玉簪》,于1956年10月,由杭州越剧团演出于新中国剧院,得到观众的好评,首演几十场,场场客满。接着,各越剧团争相上演。京剧名演员黄某特地亲临观看,索要了剧本,准备改成京剧上演。剧本也于次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演出不是风平浪静的,当时还有些人认为《碧》剧是宣扬封建道德的,甚至见诸报端,但却获得文艺界某中央领导的首肯,认为“《碧玉簪》不能简单否定,值得研究”。此后,杭州越剧团携带《碧》剧演遍上海、南京以及福建等地,均得好评。1962年,该剧经上海越剧院缩编,拍摄成彩色电影,放映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