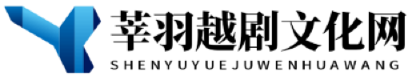12月3日晚在厦门小白鹭艺术中心观看的越剧《大道行吟》大概讲了这样的故事:孔子在鲁国难以推行自己的仁道,鲁国的国君连一盘祭肉都没有给他吃,于是孔子愤然离开故乡,带着他的们周游列国。
在卫国,卫灵公把他的仁道,曲解为“桃仁、杏仁、花生仁”,让他深叹“礼崩乐坏”,入匡城,孔子误陷仇敌之间的杀戮而入狱,险些丧命。
逃脱囹圄之灾后再赴卫国,于是改头换面的上演了“子见南子”一场戏,美若天仙的南子,慕孔子英名劝其留下,居然说出“文化人蛮有个性的嘞”这类时下语言。
面对南子的浅薄卫王的昏庸,孔子再次上路,十多年间历经十三国,一路颠沛流离“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人理会他的仁政和大道,但见战火连绵弱肉强食民不聊生,暮年孔子只得重归故国,潜心修学终老穷困之中。
所谓精彩,是觉得这出戏确是大气磅礴,舞台基础空间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大型车架,随着孔子的脚步,其时空运动和转换相当自如,准确找到了流动载体。
所谓精彩,是觉得这出戏的灯色光影异常绚烂空灵,随着戏剧氛围和人物情绪的变化,或纯净如水或烂漫如霞,铺展收缩有度,明暗强弱有序,各类电脑灯的投入量相当之大,惊叹杭州越剧院真是财力实力雄厚的大团。
所谓精彩,是觉得这出戏的演员确是梨园名伶,做功唱功俱佳,阵容整齐,扮相俊美,特别是主演石蕙兰饰演的孔子相当投入,人物状态和自我感觉都拿捏得比较准确,喜怒哀乐举步投足不掩圣人之态。
所谓精彩,是觉得这出戏的服装和造型精美又不失古朴,其艺术成就笔者认为更高于其他各艺术部门。
说到此连我自己都急着要说说为什么会困惑了,说这些并非完全针对别人的一个戏,而是为了给自己今后工作的一个思考。
我一直在想越剧《大道行吟》为什么非要写孔子呢?即便写了、演了,为什么非要采取一种貌似史诗般的框架呢?这和越剧这样一个载体连接在一起合适吗?
因为没有吃到一坛祭肉,孔子愤而出走,这一人物行动的基础动机显得浅显而勉强,甚至是太简单化了;剧中积极入世却怀才不遇的孔子,一路所遇,激发了他的一腔愤懑,始终愁容不展愤世嫉俗,一片空泛的情绪在蔓延,没有看到一个智者乃至于圣者的心灵智慧,至于剧中常常引用的孔子箴言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更显得无从附着。
这出戏很显然是想正面书写孔子,但“子见南子”一场、子见卫灵公一场,却极大引用了时下的所谓“时尚”元素,卫灵公对“仁”的调侃,南子对孔子的调情,似乎又在试图“解构”“颠覆”什么,如果用当下“满足观众观赏性”的意图来解释,真是有那么点自己给自己挖坑的感觉。
编导并没有真正深入的去研究孔子,也没有吃透和掌握必要的历史素材,特别是没有提取出周游列国十多年间,孔子的精神演变实质,整个戏对孔子的描述非常草率。
那么写了、演了孔子,是为了拓展越剧的表现领域吗?时下坊间热衷于所谓拓展某一剧种的表现领域,不问青红皂白,不顾自身的强项和弱项,大都从概念出发,弄得一些戏不伦不类,尽失传统之美,未见发展之优,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复古复的是最迂腐的古,维新维的是最皮毛的新”,这又牵扯到了戏曲的继承与发展这个命题了。
众所周知,越剧最擅长风花雪月委婉凄美的故事和人物,如果说这是一种局限不如说这是一大特色,比如,秦腔演《千古一帝》塑造秦始皇,无疑从载体到表达都是合适的、准确的,秦腔势拔五岳、苍凉雄迈的高亢唱腔,势必能把秦始皇表达的淋漓尽致,而越剧塑造的林黛玉、祝英台,贾宝玉、梁山伯则是工于哀怨凄美,风流潇洒,不同的剧种拥有不同的优势,不同的剧种拥有不同的擅长,又何必非要扬短避长在越剧里去塑造楚霸王,在秦腔里去塑造张生呢?
《大道行吟》里孔子率领们一路走来,是基本的舞台叙事,也就是说,我们从头到尾,基本上看到是清一色的男性人物,这出戏还不像越剧《赵氏孤儿》那样以男性演员出演男性,而是严格遵循了越剧的古老传统:所有男性人物均由女性演员来扮演,我非常尊重《大道行吟》里登场的所有扮演男性的女演员,她们都相当出色,就表演本身来讲是第一流的,但问题是,满台的男性人物都由女性来扮演,面积之大、人数之众,可谓空前,看起来一直很别扭。
这里隐伏着一个大问题,既然固守了越剧的传统方式,那越剧作为一个对演员性别有着严格界定的特殊剧种,为什么非要去托举一个必须是众多男性人物才能完成的题材和故事呢?这是在发展越剧的表现领域还是让越剧的优秀传统遭遇了当下“现代性”滥用的尴尬呢?!
一般来说在越剧里,男性人物的出现是有着某种默契式的限定的,肯定不会多,更不会很多,《大道行吟》已经不是“很多”,了,而是满台皆是,很多瞬间会感到这哪里还是越剧,如果看类似的场面又何必去看越剧呢。
越剧中除小生能跃进到主要人物外,其他男性人物行当一般居于次要角色行列,而孔子是老生演员饰演,尽管石慧兰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但老生的优势表达显然不是越剧最擅长的。
再说灯光,其所有艺术成就用在这出戏里是不是合适呢?那么多的电脑灯构造了一个时下晚会式的绚烂奇异,孔子沉静庄重的身影活动在一个如此晚会化的氛围里,致使他的魂魄不翼而飞,总觉得他要张嘴唱流行歌曲似的,要知道灯影光色的好看漂亮是有着不同精神气质的,没有相应戏剧气质的好看漂亮实在是太泛泛化了。很显然,这里有一个“度”需要控制和甄别。我们的戏剧光效受大型晚会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毋庸置疑,越剧《大道行吟》的演出呈现,如果大而化之的议论算是精彩,演员、舞美、灯光、服装乃至于道具,都是高水准的,但它在剧种表达原则上出了问题,比如有些戏,你看舞台呈现的各艺术部门都很一般(这个一般也要看视角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多技术的包装,很朴素)但它在剧种的表达原则上是准确的、是舒服的,它所演释的内容是只能由这一剧种才能完成的,这类戏的这个“一般”其实更是“精彩”。
我们似乎太多的去理解去追求浮华的声色,太多的去制造去索取功利化的表达,偏移就会大规模入侵,中国戏曲的那些优雅和优美荡然无存。
在本届中国戏剧节的第一次点评会上,一位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某大学的东方戏剧学者发出了告诫,她说她作为中国戏曲的爱好者、研究者和崇拜者真诚的希望,千万要保护住中国戏曲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千万不要将西方七八十年代的东西叠加在中国戏曲里,致使中国戏曲失去了它伟大的传统。这位女学者说这番话的动因,恰恰是在评论了同是越剧的《红色浪漫》之后。
这出戏我没有看过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判断她的话所针对的现象和我的“困惑”非常相似。(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