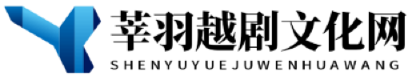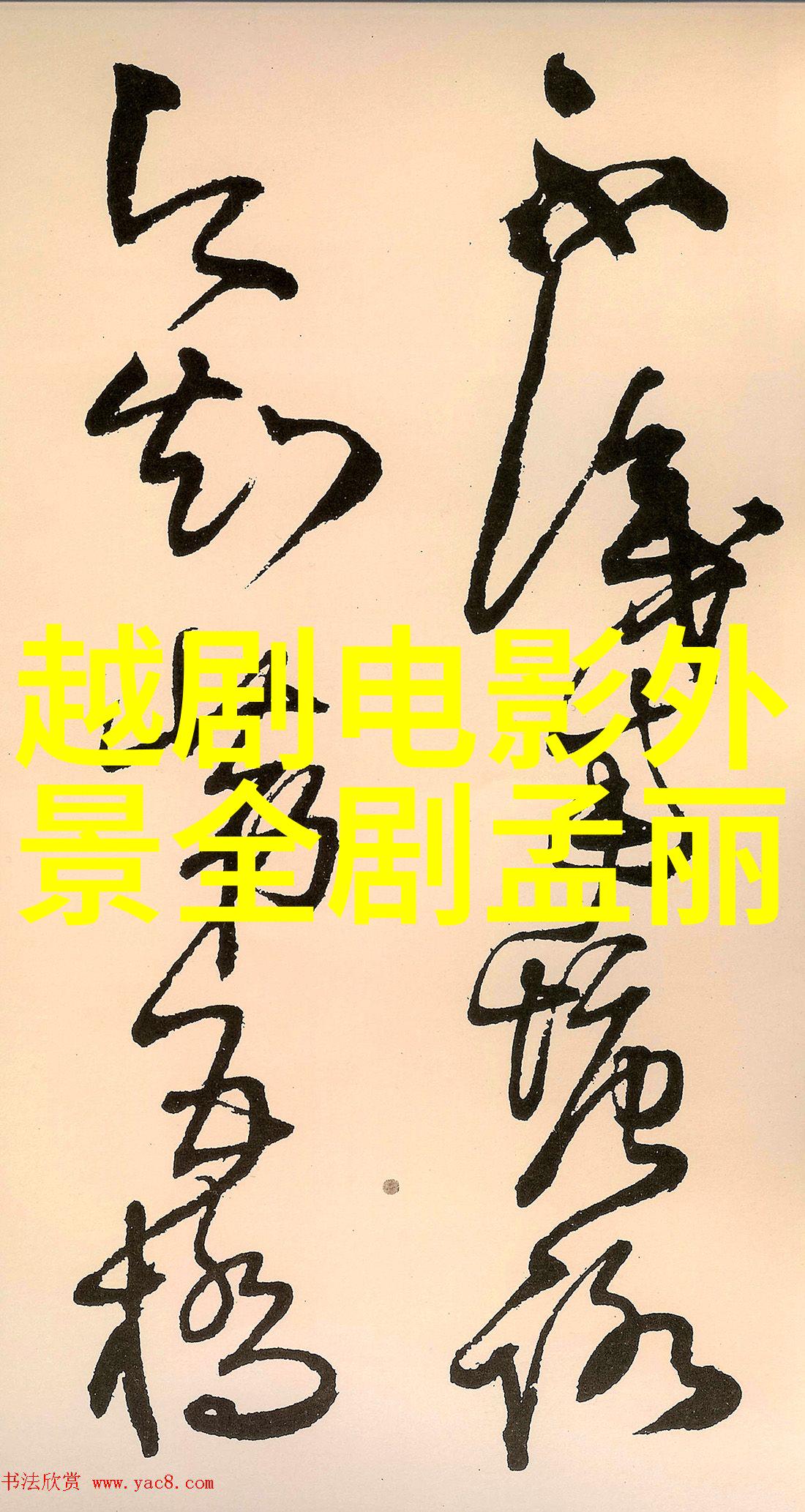
近日,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举行的第二届越剧艺术周上,由上海越剧院带来的经典剧目《红楼梦》吸引了首都观众纷纷前往观看,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在国内,从南到北的戏曲爱好者对越剧《红楼梦》都不陌生,主要还是因为那部空前绝后且又独具的彩色电影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在今天,研究者应当在见到地方戏繁荣复兴的可喜局面的兴奋之余,再做一次深情回顾,看看前辈戏曲大师是如何创下高峰,给后人留下永恒的杰作的。
众所周知,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与另外三部古典小说不同的是,自其流传坊间以来,书中大约四百个人物,性格各不相同,见仁见智。一般来说,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足智多谋、鞠躬尽瘁,再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形象就是半人半猴、有胆有识。诸如此类,普通人对这些典型化形象的理解大体一致,唯独《红楼梦》写出来的一堆男男、老老少少,让每个读者都给他们蒙上不同的性格底色,可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起“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曹雪芹简直完胜莎士比亚。基于这一原因,历史悠久的昆曲及梆子、高腔等剧种都不涉及《红楼梦》题材的戏,怕的就是看多了原著的妇孺对戏台上演绎的宝玉、黛玉心生偏见,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像。后来,京剧几度遭遇戏曲改良运动,剧作家如欧阳予倩等编演了几出《红楼戏》,最出名的莫过于梅兰芳的《葬花》,但也同样受到激进派文人鲁迅的无情笔伐。再后来,就连梅兰芳自己也厌弃了包括“红楼”戏在内的古装新戏,回归正统。总而言之,在越剧《红楼梦》诞生之前,那些红楼戏的生命力都被时代浪潮吞噬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越剧从浙江一带的乡野小调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剧种。这期间,演员袁雪芬演过林黛玉的戏,尹桂芳、徐玉兰分别演过贾宝玉的戏,这些零星的折子虽小,却都赚到了可观的收入,也有过一定的社会影响。直到1955年,剧作家徐进完成了整本《红楼梦》定稿,确定了全剧主线就是宝黛爱情悲剧,去掉小说中一切与这条主线关系不大的细节,有意突出封建大家族的礼教吃人的现实以及宝黛二人在青春年华的种种叛逆。这套剧本出炉,算来竟有600多句唱词,较之越剧传统戏的剧本多出一倍。不得不说,这对演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何况懂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出戏好与不好,光从平面的剧本是看不出来的,必须是立体式舞台呈现足够抓住观众的耳目,才算得上好戏。且看当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彩色电影是戏曲影片中上座率最高的,静场录音也是电台戏曲节目中点播率最高的,而中国唱片社发行的唱片数目突破三百万,为戏曲唱片销量之冠。
现在当人们可以亲临剧场欣赏充满活力的名家新秀再现经典时,同样可以在家重温那部由徐玉兰、王文娟联袂领衔主演的电影。范本终归是范本,只有难以逾越的才叫高峰。话说1957年王文娟首次演出林黛玉,已经31岁。事实上,为了艺术一向尽力保持身材的她,在那时仍然曼妙清秀、婀娜多姿,塑造20岁不到的小姑娘也是游刃有余。与其说是这部电影让她被更多的北方观众熟悉了解乃至折服倾倒,毋宁说导演在安排角色时选对了人。要知道,那个年代是越剧最火的阶段,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多如过江之鲫,只是在气质上不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像王文娟那么吻合的,在内行称之为“对路”。前文说过,以往的剧种不敢演“红楼”戏就是因为怕女演员一出场,大家都认为不像林黛玉,偏偏王文娟塑造的这一形象日后成了林黛玉的活标本。说到底,这是戏曲艺术独有的魅力与优势,它总是在鲜活的剧目中通过不同的意境给出一个个意象,这些意象就是带“范儿”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比小说中更有味道,才让人们觉得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另外,贾宝玉也被徐玉兰演活了、演神了、演透了。徐玉兰自己也曾承认,她在众多演过的角色里,最喜爱的还是宝二爷。而在她饰演这个角色之前,尹桂芳早已借着这个角色红透大江两岸。换句话说,在电影还没有问世时,尹桂芳所唱的“宝玉哭灵”一大段唱腔早已成为越剧戏迷的流行歌。尹派的特色是低沉婉转,类似京剧须生中的杨宝森一派。徐派的特色相反,高亢激昂,类似京剧须生中的高庆奎一派。在那时,徐玉兰硬是把宝二爷的唱腔唱得响遏行云、荡气回肠,令人惊叹、叫人沉醉。
徐玉兰在创造角色时,不仅虚怀若谷地向尹桂芳请教,吸收经验,还向锡剧名家姚澄问道,取长补短。除此之外,她还反复阅读原著,体会宝二爷的心情、秉性、命运。由此笔者想到,目下有很多戏曲演员总是信誓旦旦说要争当学者型演员,但事实上却涌现不出来涵养深厚的人才。究其原因,就是那些表明“生当作人杰”的演员过于浮躁,没有从演员、学者两个层面去拓展自己。作为演员,应当怀着见贤思齐的心态向同行找差距、比高低。作为学者,应当抱定“书山有路勤为径”的信念去故纸堆中寻觅角色体验。试想,如果80后、 90后的越剧后起之秀们也能也像徐、王那一代人一样敬业,越剧未必不能再度辉煌。当然,此次演出无疑是成功的,我们向经典致敬的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