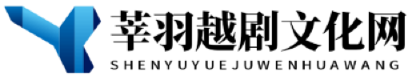茅威涛率领浙江越剧小百花,以全女班的形式在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陆游与唐琬》,引起戏迷关注。陆游是历史上有名的爱国诗人。越剧《陆游与唐琬》没有写他的爱国壮举,而是表现他的爱情生活,写他与妻子唐琬的悲欢离合。这使得该剧既是一出“文人戏”,又符合越剧本体,接近传统观众。 起源于“的笃班”、形成于旧上海平民舞台的越剧,本质上是比较通俗而平民化的,与“文人戏”有些距离。茅威涛有志于在新时代使该剧种走向知识阶层,实施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陆游与唐琬》最为稳妥。正如傅谨先生所言,它成功地缩短了越剧与文人趣味因历史原因而造成的距离,将越剧人文内涵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又不以牺牲平民性作为代价。茅威涛台风好、气质好,所扮小生有书生气,演陆游非常合适。观众的掌声既是给茅威涛的,也是给女子越剧的。 越剧的女班自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嵊县出现,然后进入上海,至三四十年代大兴于市,致使男班自然淘汰。回顾越剧正式形成之后出现的名家,无论是“三花一娟”还是“十姐妹”,全是女性。越剧在全国打响并获得传唱的名剧,如《红楼梦》、《梁祝》、《西厢记》、《追鱼》、《情探》、《春香传》等,绝大多数由清一色女性表演。女子越剧是越剧的亮点,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显著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风行全国的现代戏运动背景下,产生了越剧的男女合演。随着“”开始,才子佳人被赶下舞台,女子越剧进一步失去了依托。然而,艺术是需要遵循其内在规律的。让越剧去同别的剧种比“阳刚”,是舍本求末;让越剧放弃“女小生”,是扬短避长。六七十年代一些男女合演配合形势的作品,基本上没有赢得观众。改革开放之初,越剧界的有识之士提出拨乱反正,为女子越剧正名。在观众的呼唤下,上海几位女子越剧代表性人物重新露面,在文化广场开清唱会,引起轰动。但热闹之后,男女合演仍被视作主流。 就在此时,浙江“小百花”涌现出来了。“领军人物”出现在嘉兴地区,一朵朵花儿先在诸县市怒放,继而集中到省会杭州,巡演至香港,挺进到上海。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第一个剧目《五女拜寿》,以其满台美女,小桥流水般的阴柔特色和婉约的流派唱腔,征服了观众,长演不衰。探究“小百花”之名:“小”者,“小白长红越女腮”,清一色的越乡少女也;“百花”者,乃是在当时几乎由男女合演“一花独放”的局面下,要求“百花齐放”之谓也。这是为女子越剧争取合理合法存在空间的“斗争”。 当年《五女拜寿》在沪盛演,对上海越剧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而引发学术讨论,冲破原来的观念和管理约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是,沪浙联动,理直气壮地重振女子越剧。这一过程,大约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告一段落。女子越剧回归主流,浙江“小百花”功莫大焉。 缔造浙江“小百花”的主要功臣是顾锡东先生。在20年前那一段众说纷纭的日子里,顾锡东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论争上,而是埋头搞女性化古装越剧的创作。他先后为“小百花”写了《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唐伯虎落第》、《汉武兴邦》、《汉宫怨》等作品,可谓“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与当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习惯性思维,恰成异趣。 在20年“小百花”事业的延续过程中,自然形成了茅威涛这样一个核心人物。茅威涛是尹派女小生,气质儒雅,其驾驭角色和控制舞台局面的心理能力,为越剧演员中所罕见。近年来,茅威涛作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努力在不失女子越剧特点的前提下,提升越剧的文化品位;又尝试以股份化为标志的剧团体制改革,在越剧产业的市场运作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今天,当我们为顾锡东先生的故世感到惋惜之余,又庆幸有茅威涛这样的有识之士,把浙江小百花的接力棒紧紧握在手中。祝愿越剧这朵长三角地区的艺术奇葩,能够“全女班”和男女合演比翼齐飞,与时俱进。 (摘自 《华东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