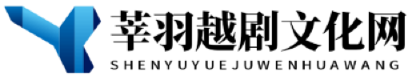在外国戏剧的研究中,既应该包括文本研究,也应该包括舞台研究。但长期以来,在外国戏剧研究中,文本研究盛行,而舞台研究衰微,造成了外国戏剧研究中的缺失。在外国戏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莎剧不是影响最大,也不是影响最早的。而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当代戏曲舞台上,无论是易卜生的戏剧,还是其他外国戏剧家的戏剧,改编为戏曲的数量根本无法与莎剧相比。莎剧改编为众多的中国戏曲,拿到中国戏曲舞台上进行演出,可以说是一花独秀。这种现象值得外国文学研究注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多次被改编为多种中国戏曲莎剧,其中由绍兴小百花剧团改编的《马龙将军》将话剧形式的莎剧与音舞性很强的越剧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莎士比亚的名字已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联系起来了,并且受到了喜爱越剧与喜爱莎剧观众的共同赞赏。这样的改编符合当下世界莎剧舞台演出的发展趋势,为世界莎剧舞台又增添了一朵越剧之花,成功地实现了文化与艺术之间中西方的对话。一、艺术转型与莎剧的当下性在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中,越剧是改编莎剧较多的一个剧种。中国戏曲包括越剧对莎剧的改编,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戏曲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寻求当下性、现代性,突破原有的地域范围,获得更大范围认知的一种内在驱动力的表现。由于有了这种内在驱动力和改编世界著名经典戏剧,特别是莎剧的强烈愿望,那么,在全国女子越剧中独树一帜的绍兴小百花剧团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以下简称《麦》剧)改编为《马龙将军》(以下简称《马》剧)也就在事实上为实现莎剧舞台演出的当下性,既为观众提供了欣赏越剧莎剧的机会,又为不同语境、戏剧观建构起来的戏剧带来了理论对话的必要。 在绍兴人文环境浸润下的越剧,以其高亢、激昂的绍调、过硬的武功,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把江南水乡之柔美、婉约、华美、优美“演绎到了极致”,使越剧在绍兴显得比别处多了些雄健之气,其天然的表现范围似乎更加宽泛,以这样的风格来搬演莎氏的《麦》剧应该说就有了成功的基础,但基础仅仅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采用越剧这种形式改编《麦》剧,可以通过改编,突破原有越剧的表现范围,检验、增强越剧的表现力,让越剧与莎士比亚接轨,通过改编使越剧能更加贴近当代。跨越地域的限制,实现经典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尽量传达出莎翁原剧的涵义,让中国化、越剧化的《马》剧走向中国观众,并在跨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实现越剧改编莎剧的现代化意义。戏剧属于“文化之最直接呈现于感觉的层相”的艺术,要将《麦》剧情节中国化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使莎剧精神中国化与莎剧戏曲化达到水融的程度,怎样在莎剧和越剧两种不同戏剧观形成的戏剧中间,在各有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戏剧之间找到契合点、融合点。 改编莎剧,无论是采用话剧形式,还是采用戏曲形式改编,在舞台上都有将改编的莎剧定位于中国某个朝代的这种做法,或者采用模糊处理的方法,如李健吾将《麦克白》改编为《王德明》就是定位于初唐。英国女演员兼导演玛格丽特·韦伯斯特相信“莎士比亚会欢迎并使用今天剧院所掌握的视觉手段;并且相信,一次莎剧演出应该给舞台带来的那种视觉美素质。”我们看到《马》剧把戏剧发生的年代隐约定位在春秋时期,舞台上远古饕餮文的运用,在视觉与想象上,暗示了这点,饕餮下方悬挂的条幅,即代表旗也代表人,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戏曲中“守旧”的变形,这是一种十分中国化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将中国文化融入莎剧,使之走向西方观众,为当代莎剧演出带来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即莎剧的现代性,表现为不同民族、不同艺术对其不断的改编、演出和阐释。 这样的改编,使中国人通过越剧了解了莎士比亚。莎剧和越剧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中跨越了东西方文化,让越剧观众在他们所熟悉的外在文化形式中感受到莎剧内在的深刻哲理性和人文主义精神,这是《马》剧之所以获得越剧观众喜爱与莎学学者肯定的原因,也是莎剧在当代社会和不同语境中一次成功的文化转型。二、主题与形式之间的重构与替换越剧与《麦》剧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改编基础呢?这种基础就在于戏剧尽管有其历史个性与独特风格,但也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当其向“本质属性归复”,就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按照编剧孙强的话说:“我们走的路子是忠实于原著精神,并将西方的故事完全中国化。”将莎氏悲剧表现人性的深刻性植入越剧之中,尽管在植入过程中,对所谓“人性”的挖掘不可避免的有所偏移,但有助于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舞台装饰的华丽‘奇观,(Spectacle)掩盖戏剧精神内涵的贫弱或荒谬”表现在《马》剧中,则反映出“每一个陈述都有一个作者……对话反应使话语人格化”,这个作者也指表演者,“陈述被看做是人们的观念表达,未出现的陈述被看做是另一种观念的表述”,即莎士比亚的表达与越剧的表演。在《马》剧的开场中,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代,英气勃勃、俊美的马龙以内唱“八百里狼烟俱扫尽”出现在观众面前: 今日里展宏图立功勋,看天下英雄更有何人?……贤妻妆楼将我盼,粉墙绿竹将我迎。归心似箭催战马。 “看天下英雄更有何人”的一大段唱腔表现了英豪之气,马龙以干净利落的“一字开”,跨步、疾走、踢腿、分袍,转体“抢背”,“转身僵尸”一气呵成的亮相后出场,英气逼人的马龙尽显英雄豪杰的豪迈气质。三位巫神预言的,得胜班师,老皇恩赐,官上加官,封侯又拜相,虽然令其心有所动,但面对妻子姜氏杀皇登位的煽动和劝诱,马龙断然拒绝谋逆,“诸侯争霸,天下多事,望我执剑护民保家邦”。面对一再的“这皇帝宝座,老迈昏庸的皇帝坐得,懦弱而无寸功的太子坐得,你,盖主功高,偏偏就坐不得吗?!”的劝诱,马龙“明知道窃弑君忠义丧,却难挡金冠诱人闪华光,心魔驱起了黑暗的,剑在鞘中声振响,焚心似裂五内乱。”从“身负重任应报国,跪拜深深谢君王”,到“杀人如麻血里洗手照样是圣人”,再到“却是终日惶惶噩梦纠缠只落得众叛亲离冷冷清清”,在这几个层次的心理较量中,扮演马龙的吴凤花利用越剧长于抒情的特点,比较准确地诠释了人物心理转折的复杂层次,即莎氏本身没有预见到后来的“被集体解释的方式所崇拜的权力表现方式,成为马龙“精神上的寄托”。从互文性角度观照,《马》剧将莎氏的《麦》剧在深层次的改动中,利用越剧的艺术形式,在范派越剧声腔的基础上,围绕演员嗓音特点和人物性格特征进行唱腔设计,有机融汇了绍剧、京剧以及女子越剧的行腔风格。吴凤花“紧紧把握住马龙坚韧、固执、贪婪、权欲,以及失去理性的狂傲、凶残和多疑,她没有去模仿别人扮演麦克白的魁梧和暴戾,因为需要她扮演的是越剧化的马龙,马龙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恶棍,既有思考又有灵魂的煎熬,行为极端,双重人格,性格复杂的艺术形象。”《马》剧中的伦理判断把人当作目的,其“精神凸显了每一个个人的道德价值”。《马》剧中的吴凤花以扮相俊美成为戏曲史上的第一位女性“麦克白”,他(她)以繁复的做功和过于注重肢体语言的表达,力图体现人物的心理活动,音色宽厚而明亮,在真假嗓的结合上,唱腔跌宕起伏,使观众对于英雄失路在批判的同时,更多了一层同情,也有别于我们看到的所有麦克白。而饰演姜氏的陈飞,唱腔清脆、委婉、甜润,扮相娇艳多姿,“运腔华彩流畅”:姜氏女此生好作梦,梦中常捧着皇后玉玺,……平叛英雄众心系,正可趁势做皇帝。 从“可怜英雄志,全为他人忙”,到“玉盘金盏齐欢呼,皇家威仪盖世无”,再到“满手的鲜血难、难、难、难洗清,凶残一娇媚,野心一柔弱,美丽一奸诈的特点,在其身上得到了统一,“出现在舞台上的姜氏有异于越剧舞台上常见的旦角之处在于她是一位有野心,有决断,有担当的女性,而不仅仅是一位功高盖主的将军的贤内助。”在《马》剧中,她以冷若冰霜的形象气质和传神传情的表演技巧.既将女性美丽温柔的一面展现了出来,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阴险奸诈的女野心家、阴谋家的性格特征,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马》剧通过这种形式之间的再次建构与替换,将《麦》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心理层次的变化,“移到一个新环境中,继而载入自己的文本与之相连”,甚至通过这种戏剧形式之间的转化,以越剧的审美方式呈现出更多侧面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矛盾。因为这种再现与重构,不会是莎剧的文化架构整体移入越剧。因为“任何文化交流都离不开本土化过程,不仅对外来文化的解读,而且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永远不可能是对该文化本义的复制,期间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莎剧并不存在““情节的整一性……”在这个现代性上,中国现代戏曲与莎士比亚是相一致的。”而且“任何莎士比亚的剧本的正确演出都要依赖于富有想象力的理解,藉此才能再现其人性。”《马》剧就是在这两种审美理论和两个不同文化圈所孕育出来的不同文化、不同艺术形式的碰撞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三、美在模仿与虚拟之间由于西方悲剧在本体上属于模仿的艺术,因此便形成了形态上特有的美学风貌。西方戏剧重模仿,注重模仿生活本身的“真”。美学风貌呈现为:悲剧的舞台形态基本上是再现生活形态,因而它基本上不作叙述的表现……在西方悲剧中,其内心的活动就远比外在的动作来得主要。而对于《马》剧来说,既要在改编中表现出《麦》剧秉承“人文主义者逐渐发展出的重人的意识”的人文主义悲剧精神,又要在形式建构中,以展现越剧艺术“美”的方式来呈现的。为了较好地解决不同戏剧观下产生的戏剧,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建构与转换,表演者“浓墨重彩地剥开马龙的内心世界,利用越剧——长于抒发内心情感的唱段,向观众展示谋杀老皇前后,马龙夫妇波澜汹涌的内心体验,揭示吞灭人性和毁坏社会的主题。”《马》剧中唱段的作用就等同于《马》剧中的独白,在时而高亢,时而低回,时而亢奋,时而抒情的唱腔中,其中的惨杀之事、心理矛盾、情感冲突被衍化成了观赏性极强的歌唱、程式表演。在“百官宴”上,当了皇帝的马龙在雄浑的音乐和激昂的鼓点声中所外化的长剑舞,以武功刻画了此时马龙的精神状态和志得意满的王者之气。在当今“艺术为人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下,“单纯靠维护传统无法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所以观众在痴迷于演员的身段、程式等精湛表演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之中通过外化的程式,通过言语(台词)与歌唱(唱腔)之间的对话,通过“力量”与“柔弱”之间的互文性,通过内心与外表的转化,用越剧方式洞悉了人物的内心变化和人性的堕落,从而使观众惊叹不已。对越剧演绎莎氏悲剧来说,通过这种既刚且柔的唱腔、程式表演,在扩大越剧表现力的同时,既成功地诠释了莎氏悲剧的精神,又通过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美的技艺)的刺激,超越了对内容的理解。 越剧中的悲剧主人公往往是女性,这为改编《马》剧带来了难度。而这一难度恰恰为《马》剧中马龙的野心、罪行的表现,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表现空间。马龙的扮演者吴凤花为著名梅花奖获得者。女性扮演男性,越剧的这种特性与莎氏悲剧要塑造英雄,表现英雄的毁灭恰恰构成了强烈的性别冲突,但却也因此获得了莎剧表演的越剧意义与现代意义。而姜氏的毁灭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明代曲论家祁彪佳的说法,“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中国悲剧苦情美感的获得,激发起了观众的怜悯和同情。所以,《马》剧的再现生活形态的悲剧精神与复杂的内心矛盾冲突与越剧女扮男装设计的刚烈、流畅的唱腔、程式结合在一起,用越剧音舞去演绎《麦》剧的故事,阐释其人文主义精神,将模仿生活与虚拟性的审美表演融合为一体,既比较深刻地阐释了《麦》剧的批判精神,又在戏剧形式改变的基础上建构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其创新的表现形式,将悲剧精神外化于程式、唱腔和表演之中,以情感的大起大落,矛盾的纠结与化解,内心的阴暗与外表的俊美,行动的迟疑与果决融入《马》剧中,将《麦》剧中的爱、恨、情、仇用越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思想透过越剧审美的形式展现出来。当悲剧精神得以确立后,再使“人立于情,戏出于情”,那么既能够从越剧审美、观赏层面上表现《麦》剧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理内涵、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心理活动,也在哲学、美学、舞台表演层面上丰富了越剧“诗情画意,塑造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变化的表演空间。 《麦》剧与《马》剧的对话、互文性,既是主题上的继承、开掘、建构与挪移,也是外在形式上的替换与创新,更是审美、艺术、文化之间的成功转型。《马》剧所遵循的改编策略就是在力图完整表现其主题的人文主义精神时,以越剧重构话剧(莎剧)这种艺术形式。这样的改编表明越剧的美学理想和莎剧美学精神通过《马》剧在审美层面上进行了一次成功嫁接,这样的嫁接表明,无论在外在形式、内在思想内容和审美视点上,越剧与莎剧对话和互文性都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审美天地,并成功地跨越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