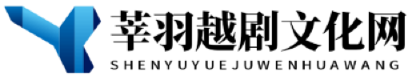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手记】 3月,春和景明。杭州曙光路59号,中国越·剧场即将亮相登场。 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的新舞台。去年退休卸任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团长之后,她即出任百越文化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由阿里巴巴马云、绿城集团宋卫平、“小百花”越剧团等共同出资发起成立,将主要从事中国越·剧场的整体运营。 除了经营剧场外,茅威涛的新戏江南音乐剧《三笑》正在排练中,即将作为中国越·剧场开幕大戏登台亮相。此外,她的公司还投资了英国国家剧院制作的舞台剧《狼图腾》,并联合投资制作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音乐剧《大鱼》。这两个剧有望在国内演出中文版。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国内外的游客到了杭州,除了逛西湖,喝龙井茶,还能够到我们的剧场看一场越剧。”茅威涛志在长远。 即将到来的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也是越剧诞生113周年纪念日。 茅威涛 “越剧小生第一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五朵金花”之首。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传承人。17岁从艺,22岁赴北京参加国庆演出,自此成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台柱小生。1999年起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 当代越剧改革进程重要代表人物。以现代人文精神赋予越剧行当以独特魅力,在国内外拥有众多茅迷,全球各地自发成立“茅迷协会”,拥有越剧演员最广泛的“追星族”。“力图让自己的每个剧目和每场演出都具有越剧史的意义,进而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写越剧史和更宏观的戏曲史。” 学者傅谨教授如是评价她的价值。 退休了,也准备唱到60岁 心目中“小百花”的未来是日本宝冢 张英:突然就退休了,还会演戏吗? 茅威涛:《寇流兰与杜丽娘》从伦敦演出回来,我就开始想退休的事情。作为演员,当然还想接着演戏。在体力还好也有好剧本的情况下,我还想突破一下自己,再演几个戏。我给自己定到60岁。如果没有完全发胖,扮起来就算不能玉树临风,但形象还凑合,嗓子条件还好的话,我准备唱到60岁。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规划。 60岁以后,我真的不唱了。我肯定不会像以前的老人家,身体吃不消,就演一个折子戏,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如见好就收,退下来当老师去。这几年,我同时兼任了浙江音乐学院、浙江职业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在百越文创的工作之外,我会多花一些力气,培养年轻人才。 张英:回顾当团长的这19年,觉得你给“小百花”带来了什么? 茅威涛:我当初当团长,承诺给大家每年增长百分之三个点。我没有食言,每年都做到了。我曾经说“吃咸菜也要把越剧唱下去”,到后来发现,光吃咸菜越剧是唱不下去的,我改成“唱越剧凭什么买不起房买不起车?”后来大家也都有车有房了。 “小百花”的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在相对体制内的情况下,已经非常市场化、非常先进了,符合今天的时代需求。演员收入也还可以,多演多得,演好多得。以前我们演出,大家都不愿意跑龙套。现在,根本不需要动员,不用做思想工作。因为场次是一个标准,按场次拿钱,有些一级演员也愿意去跑龙套。就是去跑个龙套,也还要看认真不认真,效果怎么样,竞争上岗。 当然,戏演好演多,你成角儿了,当了主演,你的演出费跟同台的演员就落差巨大,马上买车买房子。其他演员有意见,我说“你们有本事也像她这样唱出来当主演”。当团长的这些年,我用了一套相对企业化管理的机制,没有演职人员不干活可以拿钱的。 张英:今天的“小百花”,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剧团吗? 茅威涛:我当初的规划,应该说都变成了现实。“小百花”越剧品牌起来了,戏的质量一直追求艺术精品,有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和美学形态。我们的演员梯队也非常合理,中生代和新生代演员都成长起来了。 日本的宝冢剧团,是女子剧团,她们在东京、大阪和本地有三个剧场,常年演出。她们在日本公众心目当中是至高无上的一种艺术形态。很多中小学调查,百分之七八十的女孩都说梦想是当一个宝冢的演员。宝冢能够做到这样,我希望并相信“小百花”未来也会做到这样吧。 我不仅仅是一个唱戏的演员 我在帮古老戏曲艺术找出路 张英:怎么想到办一家经营戏剧的公司? 茅威涛:国有剧团的领导,相当于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两届干下来,换一个地方去当领导。所以他们不会长远打算,没有这个动力,只会急于求成,做短期、立竿见影的项目。 日本的剧场是家族的产权,你就能够控制质量,就有品质,一代一代传下去。包括“小百花”,如果不是茅威涛,这个剧团很可能就很平庸下去了,因为它本来是很短的历史。比如说上海越剧团,哪个不牛?但为什么最后发展成那样?原因,我们都很清楚。 越剧发展到今天,我知道已经有瓶颈了,你必须要跨到市场里面去。在目前的机制下,我不可能建立一个完整、成熟的商业模式,唯有用一个企业、一个公司的办法,才能打造一个完整的商业架构。 张英:怎么说服马云和宋卫平投钱百越的?毕竟,戏剧很难赚钱。 茅威涛:马云的祖籍是浙江嵊州,夫人张英和宋卫平一样,是土生土长的嵊州人。对他们来说,嵊州话就是小时候的乡音。到现在,越剧发源地施家岱村里的百年古戏台还留存着。 八年前,宋卫平捐建的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落成典礼,邀请我去参加。在那个活动上,我和宋卫平聊起越剧艺术传承发展面临的问题。回到杭州后,宋卫平邀请了马云,我们三个人见面,从越剧人才培养、越剧艺术发展、越剧市场前景聊到越剧的专有剧场。后来我们决定组建一个商业运营公司,运营“小百花”艺术中心,改名中国越·剧场。 马云和宋卫平很有意思,我去上个洗手间出来,他们就决定让我当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马云说,阿里巴巴尽管是大股东,但是我不出董事长。宋卫平说绿城也不出董事长。我说不行不行!他们说,越剧这件事,你就是中心,我们俩辅助你。 张英:看来,即使退休了,你也是闲不下来了。 茅威涛:做“小百花”越剧团团长也好,做百越文创这个公司也好,都不是我私人的,但是我把它当成一个家园在打造。我为什么要加一个“园”字呢?除了我的生活、我的艺术,它有我的精神寄托在里面,就是我的一个家园。 我坚信,真正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文化,它一定不是流行的那些东西。它是精英文化体系里面,最和人民、大地接地气的文化——在中国就是戏曲,是民族文化里的最重要的一枝。 算起来,我们从宋始,到元有杂剧,然后明清传奇、清代花部,再到三百多个地方剧种,这样一支艺术脉络,流传下来到今天。在三百多个地方剧种都在衰落的时候,如果茅威涛能够摸索、走出一条新路来,给中国的地方戏传承和发展,提供一个范例,那一定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我们也不讲达尔文进化论,文化一定是这样,是不断地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在修正自己的一条河流。只要有一种可能,它就流下去了。我做百越这件事情,内心有一个巨大鼓舞,激励我的精神动力是什么?我是在帮艺术找出路。我不仅仅是一个唱戏的演员,我能够守住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艺术,也能够为它的发展方向尽一份心力。 演完唐伯虎和法海 接下来想演李渔和苏东坡 张英:作为中国越·剧场的开幕大戏,《三笑》什么时候上? 茅威涛:《三笑》是一个先锋实验剧,讲述秋香和唐伯虎等四大才子的故事。郭小男在负责,还有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一个老师参与,两个人一起在做。 这个戏是我们百越出品的开山之作,转型的江南音乐剧。我跟作曲者商量好,《三笑》里所有的江南小调,只要是江南的唱腔,不管越剧还是沪剧,没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只要属于江南民调,我可以集大成,什么好听就选哪一种唱腔。 我希望我的作品,不仅仅是越剧,它是属于中国戏剧,能够拿到世界的戏剧语境当中去对话的作品,能够有历史和社会的穿透力,作品能够留下来。 张英:上次听你说要演法海和尚。那个剧怎么样了? 茅威涛:《人间》会是百越文创的第二个作品。李锐蒋韵夫妇合写的小说,白蛇传的故事。有一套“重塑民间传说”图书,苏童写了一个《碧奴》,孟姜女哭长城;叶兆言写了一个“后羿射日”;阿来写的是《格萨尔王》;李锐和蒋韵写白蛇传。 几个小说全部买完看了之后,我选了《人间》。李锐老师高兴得不得了。《人间》这个作品有意思,很杭州,因为我想主打杭州旅游市场,就像编剧刘和平说的,“让你看一个白天看不到的杭州”。比如西湖断桥游过之后,你知道了这个民间传说,晚上去看这个故事。 郭小男想让我演法海,不要演许仙。如果我演法海,我怎么演?这个法海的人物到底怎么定位?《人间》最后,法海被瘟疫传染,重病,吃了白蛇的药,白蛇的药里面有她自己的血。一个捉妖人的身上,有了妖怪的血。这个时候,故事有意思了,发生了质的变化,戏剧的点有了。 郭导说,他的第一幕戏,要用一个高科技的东西。雷峰塔倒掉,观众在期待白蛇出来,结果,一本书出来了,叫《法海日记》。然后,我们通过《法海日记》讲了这个故事,最后归结起来是一个问号,无解,人永远就是这样在叩问自己。 张英:你说过,你对李渔和苏东坡也感兴趣。 茅威涛:我接下来希望演一些有文化厚度又充满情趣的人物,年龄上略微跟我的年龄接近一点的。因为我不能再演《梁祝》了,再演十八岁的梁山伯是装嫩。 这几年我在接受采访和讲学中常说要用李渔这个角色金盆洗手,告别舞台。李渔戏演得好,多才多艺,芥子园里的楼台亭阁都是他设计的,让我非常意外。 最近我正在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越来越觉得我们杭州市的“首任市长”实在是个有趣的人物。看了之后,我想演苏东坡,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些年创作演出的剧目是一场豪赌 押上的赌注,是我的艺术声誉 张英:你一直强调越剧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什么? 茅威涛:上世纪六十年代越剧进行第二次改革,最终没有进行下去。袁雪芬老师多次谈起那次改革,她可能不满足老版《梁祝》《红楼梦》这样的越剧,第二次改革希望能够再有一个腾飞,比如越剧的声腔音乐应该怎么样再丰富?那个时候把钢琴、小提琴放进去了,以后会不会有交响乐队伴奏,做成音乐剧这样,以歌舞完全说故事? 原来越剧是话剧加昆曲,既有写实性的东西,又有写意性的东西。袁老师有一句话,“越剧是喝着话剧和昆曲的奶长大的”。我把越剧界定成写实和写意之间、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间的,一方面要体验,一方面又要有技术。是不是最后我能够走出来一条歌舞化的路?这种以歌舞说故事的总体形态,是否是我们越剧未来的一个指导思想、艺术发展方向? 王国维对戏曲有一句诠释是“以歌舞演故事”,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在找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越剧的歌舞方式。创新要有底线,“新”中要有“根”,“根”就是传统,是一定要固守的精气神。经典戏曲的台词最好别动,今人写不出古人的境界,但在表达形式和舞台呈现上我们可以创新。 事实上,中国戏曲本应像西方话剧一样,跻身剧场,在市场上竞争,成为今天人们的一种休闲娱乐乃至生活方式。它必须在创作理念上跟时代接轨。 张英:评论家傅瑾是如何评价的呢? 茅威涛:傅瑾老师和我认识多年,是好朋友。他说我这些年创作演出的这些剧目,对我个人而言是一场豪赌,我是在赌越剧的当代影响和历史发展,而押上的赌注,是我的艺术声誉。我看了他写的文章,觉得他真懂我。 中国的民间信仰和戏曲是有极大关系的。西方现代教育和文化没有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从哪里来?很多是从戏曲里来的。我小时候,奶奶、外婆跟我讲道理,都是举例讲故事给我听,那就是戏曲里得来的。 为什么戏曲越来越边缘了?因为你只是一个凝固的旧瓷器,装的是过去的酒,时间太长,今天的人不爱喝了。你表现的价值观都是过去的,你和当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怎么感动观众让观众喜欢呢?过去的意大利歌剧那么死板,但现在同样可以排得时髦和现代。莎士比亚的戏,很多欧洲国家都演得很现代。时代在变化,如果越剧还停留在过去,一成不变,不知道时代已经变了,怎么行? 我是戏曲演员,但我欣赏麦当娜,欣赏迈克尔·杰克逊,我喜欢欧洲独立制片电影,我喜欢现代舞。不分民族、国家,只要你的艺术载体能够让我接受,打动我、感染我,我都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来接受。那我的越剧,当它能感动我自己的时候,我怎么就感动不了别人呢?我还怕观众不能接受吗? 你看越剧的发展,《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为什么能成为越剧经典?因为在上世纪30、40、50年代,越剧是上海的现代艺术、时尚艺术。我们如何把传统用今天的人文精神、现代美学、现代戏剧观来诠释、承传?变革与创新,这条充满无限可能的戏曲探索之路,是否能够成为激活传统文化的样本?我相信并坚持,古典戏曲必须和当代接轨,和世界接轨。中国戏曲一定要置身世界戏剧的语汇中,去和全球戏剧对话。 国家会养着你,但半死不活的生存状态 以我的个性我是没办法走下去的 张英:怎么看待那些反对的声音,比如戏曲就应该守护传统,原汁原味,保持不变? 茅威涛:如果戏曲不发展,未来我们只能到博物馆去欣赏。越剧的观众都在变老,中青年人根本不看戏。如果只是迎合越来越少的老观众,越剧和戏曲一样,会走进一个死胡同,最后变成标本。 如果我们的传统戏曲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农耕时代,几百年不变,在现代社会生长起来的观众,完全有理由抛弃你。即使他们还在看戏,估计也是把它当成“秦砖汉瓦”,当作古董来看的。 我们有些从业人员不思进取,不学习,剧团到了当地演出,白天搓搓麻将晚上完成演出。你不改变自己,你陈腐、老化、落后,你怎么能改变这门艺术的命运?怎么可能吸引观众,让今天的观众自愿自动买票,掏钱去看? 中国戏曲的历史,方言催生地方剧种,曾经有三百多个地方戏,到现在还能演出的只剩十个了。如果我们自己不,依然停留在农业文明的印记里面,我们自己把自己弄死了。国家会养着你,但半死不活的生存状态,以我的个性我是没办法走下去的。与其这样,我不如回家相夫教子去了。 张英:你的家庭对你有怎么样的影响? 茅威涛:我外婆和外公家都是桐乡世袭的书香门第。外公的父亲是时代的桐乡县教育局局长。外婆的爸爸是当时东海舰队,航务出身的世袭家庭,那个时候叫温州海军提督。我外婆上过南京金陵女子中学,读了两年。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从小我外公外婆逼着我读《三字经》,后来读《论语》什么的。 从小我认为最幸福的家庭是什么?就像我们乌镇这种江南庭院,青石板路,家家的白墙上面爬满了青藤。窗户开着,有纱窗。然后有爬山虎、蔷薇、月季爬在那里,开着花挂下来。四合院里有天井,挂着鸟笼,有秋千架,长亭上爬满了葡萄,还有一口井,夏天把西瓜放进去冰一冰。 我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当我在事业上取得成绩,在生活里得到一些物质东西、所谓的名利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会提醒我,不要因为一点成绩就骄傲。会叮嘱我,人是这样的,要有一种很谦卑的心。我得到的所有的好,都是因为大家。所以我现在要把这所有的好,转赠给别人,带给别人。(张英) (摘自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