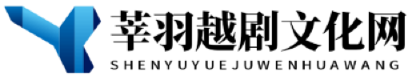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 莫不是风吹铁马檐前动?莫不是那梵王宫殿夜鸣钟? …… 夜听《西厢》,真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一段“琴心”,是越剧袁派的代表作。当初,因为《西厢记》的音带中删去了这一折,使这一段优美的唱腔沉寂多时;后来,虽然出了全本的实况录音的磁带,但因为发行的原因,并没有普及开来。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当袁派重新出道之后,很快地,这一段唱腔就风靡开来了。 我听过好几个袁派的这一段唱腔,但总觉不如原创的来得细腻微妙。从伴奏的角度讲,是越来越豪华了;然而,“琴心”是空谷足音,并不需要这些豪华的“杂音”。我是后来才听到袁老的这一段唱腔的,她唱的并不像那般“滑溜”,若断若续,边沉吟边抒怀,在单纯而清雅的伴奏烘托下,更显古典的神韵。也许,们生活在已没有多少古典气息的时代,很难感受那种含蓄的幽怀;然而,袁老也并非名门闺秀,她也仅仅亲炙过残余的古典氛围。那么是什么陶冶了老一代艺术家的敏感的心灵呢?也许,是那潺潺的剡溪滋润了那些从并没有多少艺术气息的乡村出来的卖艺姑娘吧。 可惜,这样一出好戏,于今只有袁老的音带而无音像,真是令人遗憾至极。然而,不断地细听那音带,不断地揣摩那些舞台照片,袁老的崔莺莺还是能或多或少地在我的脑中复活。《西厢记》是一出心理剧,是一对古典青年男女恋爱时的心理博弈,没有《梁祝》、《红楼》的大喜大悲;就是喜闻乐见的“佳期”一折,也被袁老删去,而添之以心理刻划的“寄方”。然而,也正因为不媚俗,才见出这出戏的功力。这样的戏,注定了它在舞台上寂寞的命运。阳春白雪,风华绝代,又怎能被轻易地复制呢? 其实,又岂止《西厢记》是这样?袁派的其他节目,也都有着类似的命运。像《祥林嫂》,多少年没有演了;即使偶露舞台,也只是片断,而且大多还是“成亲”一折,并不能见出此剧的深度。好在,《祥林嫂》有录像,有电影,多少能弥补一些遗憾。我看过故事片的《祝福》,还有最近淮剧的《祥林嫂》,但总觉不是味儿;独有袁老的《祥林嫂》,才让我感到震撼。如果说《西厢记》的难度在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变”,那么,《祥林嫂》的难度就在于刻画人物灵魂的“深”。像“厨房”一折戏,在鲁迅的原著中,只有这么寥寥几句话:“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但袁老却把她挖掘成一折戏——而且,自己参与剧本的创作。她把祥林嫂遭受心灵重创的过程,通过精湛的演技和老辣的唱腔,非常准确地演绎出来了。这一段唱,具有惊心动魄的穿透力,把人物的内心恐惧刻画得丝丝入扣,入木三分。而在“摸蜡台”一折中,则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当祥林嫂捐门槛回来,碎步小跑进入她渴望已久的祝福大堂,去摸那以前不能碰的蜡台时,那种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她想摸,却又缩回来,仔细地看看自己的手,等确信自己的罪已赎过,手已干净之后,她终于一把抱住了蜡台,嘴角翕动,时翘时垂,欲哭又笑,欲笑又哭。这一段表演,非常具有震撼力,可以说是全剧的情感,我没有见过能如此深层次地刻画人物的戏曲演员。这种内心的体验,须得演员感同身受;一般的程式化表演,根本不能刻画出来。而结尾的一大段“抬头问苍天”的唱腔,悲怆而苍凉,演惯了莺歌燕舞的越剧,真亏她还能有如此的表演力! 我常常在夜间听此两剧。夜听《西厢记》,是因为白天太杂,这样飘忽多变的内心,这样细腻优美的唱腔,在嘈杂的声音中怎么感受呢?夜听《祥林嫂》,是因为这么悲凉的唱腔,是不宜让它在大白天四散传播的,我不想破坏祥和的氛围;而在夜晚,也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私间里,因为谁也不想被这种“不吉不祥”的声音所笼罩。实在,这两剧所表演出来的艺术力量,在越剧中是罕见的。我常常想,袁派之所以一度萧疏,即使在今天,也只有二三唱得有板有眼,应该与此有关吧。作为名著,必须是演员不断向名著靠拢,立体化地刻画人物,而不像有些通俗剧,是类型化的,演员把它演成怎样它就怎样。这与“画鬼容易画人难”,是一个理儿。 袁派创立很早,历史很长。袁老演过一百多出戏,几乎就是一部越剧史;然而,也就因为太早,大多剧目已风流云散了,只留下二三有品味的名剧和一些孤独的唱段,也少有雷同的,一段有一段的风格,一段有一段的创意;然而,正因为风格多变,又让人无所适从,很难套搬。这在因袭成风的越剧舞台上,显得孤高独标,不免让人望而却步,也让人心向往之。 也许,这就是袁派的品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