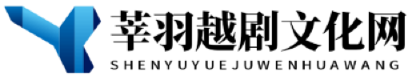今明两天,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将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两场明星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用现代人的视角对剧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因而受到津门越剧迷的普遍关注。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尹派小生、剧中梁山伯的扮演者茅威涛。她说,她是天津媳妇儿,每年都来天津看望亲朋好友,期待此次津门演出能给观众留下美好印象,同时也希望为越剧的新生,闯出一条新路。 新版酝酿十年 成就唯美童话 记者:新版《梁祝》新在哪里?您新近塑造的梁山伯有什么艺术追求与突破? 茅威涛:老版《梁祝》和同名小提琴协奏曲都是经典,已经深入人心。对观众几十年来的情感认知,不能忽视,更不能破坏。新版《梁祝》酝酿的时间长达十年,我们提出“规避颠覆,谨慎重述”这个理性定位。重新演绎这个故事,我们不想,也不能完全照搬前人的作品,那背离了我们的创作初衷。 新版《梁祝》是用现代越剧人的语汇去重新诠释这份刻入越剧记忆中的浪漫与美丽,我们追求的是如何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之上,使这个古老的传说能够打动今人。新版《梁祝》的新,在于原材料都是经典的,语言和表达与旧版是有距离的。《梁祝》是一种记忆,是“我家有个小九妹”、是化蝶、是十八相送,在尊重经典的前提下,赋予其人文的内涵,将一个反封建的爱情故事,剥去其反封建的外壳,演绎成一个以《诗经·邶风·击鼓》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主题的爱的传奇。 《梁祝》如果要去说一个故事的话是不成立的,祝父会让祝英台出门吗?梁山伯跟祝英台相处三年能不发现她是个女的吗?人死了会化蝶吗?都不会。这只是中国人对爱情的一种寄托,所以你不能做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要做成一次唯美、一个童话、一个传奇,做成歌舞,做成蝶,做成花,做成一次彻底的浪漫。新《梁祝》借助了所有对《梁祝》的情感记忆,包括对化蝶、对小九妹、对小提琴协奏曲的回忆。梁祝就是蝶,就是花,就是童话。满台不见蝶,但满台都充满着蝶,那是意象的,现代舞意象的化蝶。只用音乐、灯光、舞美,做了一个大的渲染,让观众走进剧场来,进行一次关于《梁祝》的集体回忆。 演梁山伯 要面对三个问题 记者:有评论说,茅威涛创造了一个“尹派的梁山伯”,茅威涛的梁山伯承袭了她一贯的书卷气和人文情怀。对于梁山伯,您是怎么理解和刻画这个人物的? 茅威涛:在梁山伯的身上,我看到了孔乙己的落魄,看到了范容的执著,看到了陆游的爱而不能……我需要把一个民间传说中谈情说爱的小生,塑造成为一个礼教之下的儒生,一个在情与理之间奔突,最终不得不将生命舍给深入骨髓的爱的情痴。范瑞娟老师的梁山伯形象太深入人心了。我要怎样才能重新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山伯形象呢?演梁山伯,我首先面对的是三个问题:一、梁山伯是一个男人,那么多书生里,他为什么会跟祝英台最为投契?二、当他得知祝英台是个女人的时候,为什么会将友谊转成爱情?三、爱而不能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选择死亡?在不断地改写和阅读剧本中,我开始逐渐进入到梁山伯的世界中。跟祝英台特别投契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从属性很重的人,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书生,而英台是一个无拘无束、不为功名、不为应试而读书的一个人,因此他会特别为英台的生命姿态所吸引。三年相处没发现英台是个女人,是因为他是一个严谨的书生,忠厚本分。当发现英台是女人之后,新版中《高山流水》一场里《诗经》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心心相印已经铺垫了足够的情感基础,说到这首诗,其实是几经改变才决定的,一开始想到过用《高山流水》、用《凤求凰》,但感觉都不对。直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一句跃进来,才觉得情绪上对了。 让传统艺术在信息时代得到发展 记者:你们剧团对新时期越剧艺术生存与发展的理想与实践,都有哪些? 茅威涛:中国戏剧起源于农业文化。我一直深信传统的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文脉和脊梁。如何让传统的艺术在今天这个传媒信息高科技时代生存,是每一个戏剧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越剧的百老汇,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共同效益;我们追求古典与时尚的对接,传统与创新的共存。一种艺术形式的确立,要经过漫长的历史锤炼。越剧就经历了百年的淘洗,经过新文化的洗礼,还有租界文化的影响。加上几代人为之努力,才形成了有人文底蕴的越剧。这么珍贵的遗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丢失了。 小百花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专业女子越剧表演艺术团体,演出兼顾都市、乡镇、海外不同的市场,利用多种渠道提升、拓展越剧的影响。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剧团开始走进校园,培养越剧新一代的受众群体。在今后两年,会打造中国女子越剧的驻场演出。这个理念起源于芥子园,并辅以美国百老汇、日本宝冢的现代经营理念。目前正在建设的艺术中心位于西子湖畔,保俶山下,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其设计是由建筑设计大师李祖原先生修改、完善的。(记者 陈宝辉)
(摘自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