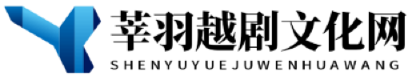省城戏缘
告别“杭大”
去绍兴下乡前的1960年暑假,我决计回乡一趟,去探望分别已经三年未见的父母和弟妹。心想一年过后,自己不知要走到哪里,说不好还会去离家更远的地方。
温、杭之间,区区几百里,居然三年不回家。这在每学期打着“飞的”随意往返的今天大学生听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对当时贫困大学生来说,却是很平常也较普遍的事。往返二三十元的路费,接近一个贫困家庭的一月生活费用。没闲钱的家庭花不起,花得起的也非所有家庭舍得。再说学校吃饭不花钱,全国只有北京、上海、杭州三地粮食不定量,学校食堂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不能去定量很紧缺的家里蹭饭,这些更是贫困学生假期不回家的理由。
这时,我开始对研究戏曲发生兴趣,课余系统地研读了许多元明杂剧,并按夏承焘老师的治学经验传授,一一做了读书札记。在回乡的旅途中,我还随身带着校图书馆借来的郑振铎主编的头两集《世界文库》,因为上头转载了当时罕见的戏曲刊本文献《西游记》多本杂剧、明富春堂本《白兔记》以及《刘知远诸宫调》等,供自己空时研读。又想到回乡机会难得,我要趁此机会到家乡瑞安和“出戏子”的邻县平阳调查一下地方戏,8月16日,临行之前,我特地去校办公室开了这份介绍信——

校办给我开了调查家乡地方戏的介绍信
我与同班温州同学叶金瓯同道回温州,把三年前离乡去省城的路程倒过来重走了一遍。
抵达温州市,先去看望了长妹春姑一家。我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都很早出嫁。长妹19岁就做了妈妈,进门时,见她正给一岁来大的女儿穿衣服。我的突然到来,令她感到意外。那初次见我的外甥女闻蝉,更是转着滴溜溜的大眼睛,惊奇地瞧着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大舅爹”。这使我感到三年过去,变化已是不小。
温州市去往家乡瑞安城还有40公里地,以前都走水路,乘坐温瑞塘河小汽轮往返。现在开通了长途汽车,但车票很不好买。正好那天有趟金华开往瑞安的长途汽车经过温州车站,一些旅客中途下车,可以临时补票,我挤进补了一张票。
空位少,补票的多,许多后来者只好提着行李,在车里随便找个空隙站着,本来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车内旅客你推我挤,吵吵嚷嚷,怨声四起。这个喊道:“啊呀,别挤了,我快被你压扁了!”那个叫着:“哎哟,你踩到我脚了,疼死人了!”说的都是带浓重乡音的“瑞安普通话”——在外头呆久了的回乡客,感觉自己还在他乡,忘了该说家乡话。一位青年用瑞安话笑骂道:“伲妳(妈的),大家都是瑞安人,还打什么官腔?”全车人顿地醒悟过来,一阵哄笑,于是纷纷地让起了座位。
乡情可以贯通血脉,消弭怨怼,增添友善与谦让。回乡的感觉真好。
离瑞城近了,隆山塔显现在眼前,越来越近。在外呆了三年,感觉中隆山好像变小、变低了,很奇怪少时随父亲登隆山赶庙会怎么会是那样高不可攀。这是见识增长、“眼界”变大了的缘故。
下了车,我用扁担挑着行李,选择那条狭小的瑞城“东小街”往家走,远远望见母亲正端着一盘泔水,去对面阴沟倾倒。家境依然很糟,母亲还是那样辛劳操持家务,心里顿时涌起一阵酸楚。
父母和两个留在家中的小弟妹,见我回家,都面露喜色。毕竟三年不见,毕竟我是“荣归故里”的大学生,而且变得壮实,这使全家人感到快乐和荣耀。邻舍也纷纷过来寒暄、道喜,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我积攒每月半斤定量配给的糕饼票,买了杭州糕饼,分给众人,小弟妹高兴得不得了。在粮食定量不够填肚皮的年代,能品尝到糕饼,简直是一种奢侈。
二弟13岁,四妹9岁,6岁的三弟已过继给人家。在国家困难、家庭更困难的年月,弟妹小小年纪,就要跟父母共捱艰难岁月,过着禁衣缩食的苦日子。
二弟崇川不知什么原因,小时不爱念书,却非常喜爱音乐。家里买不起乐器,他找来竹筒、竹竿、皮,给自己制作了一把土二胡,穿上麻线当琴弦,咿咿呀呀地拉个不停。后来父母见他这样喜爱音乐,给他一块多钱,让买了一支竹笛。他视同珍宝,整日吹个不停。再后来,他用打零工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支口琴,一学就能吹。就这样,待以岁月,吹拉弹唱,二弟全都无师自通。
在家的日子里,我还听说不久前发生在二弟身上的一桩“轶闻”:
温州戏曲学校曾来瑞安小学招收新生。二弟长相、身架、乐感、悟性等,都被考官看中,竟考上了。收到录取通知,母亲顾虑孩子太小,一人去外地过独立生活放心不下,再想想将来去当一名“戏子”,也亏待了孩子,坚决不同意让去。二弟哭闹着要去,还对母亲说:“你就当作没有我这个儿子算了。”母亲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让去。二弟在人生岔道上,就这样跟戏曲职业擦肩而过。爱子心切和受传统诗礼观念束缚的母亲,这一决定,不仅彻底改变了二弟的人生走向,也使温州地区少了一名未来可能的地方戏“知名演员”。
后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思考:所有的人生都在“选择”中经历,所谓“命运”,不过是各种“选择”的结果。正确的选择,会带来“好运”;错误的选择,会酿成“坏运”甚至“恶运”。由于年代造成的路途阻隔和信息不畅,使我没法参与二弟的“选择”。这是二弟的运蹇、我的惋惜和遗憾。
后来二弟“上山下乡”十几年,名义为 “插队知青”,实际是无业农民。回城后,生活无着落,吃了许多苦,只好凭他自学乐器经验,又自学成一名城内小有名气的木匠,靠手艺度日。直至晚年,子女成材,生活改善,酷爱音乐习性不改,取网名“乐痴”,一空便去参加瑞城“榕树下”业余文艺团体活动,弹琴,唱戏,唱歌,找到了他人生的最爱。

二弟崇川晚年找到了他人生的最爱
我见家中粮食如此紧缺,父母天天为粮食定量不够,供养不起全家发愁。我不可久待,在家只呆了没几天,拜访了几个没上大学的要好同学,看望了几位中学老师,就提早匆匆返回杭州。调查家乡地方戏的计划没有时间实现,那份学校介绍信,永远留在了我身边。
我对戏曲的爱好与钻研成果,包含着父母的爱心与劳心的灌溉。19年后(1979),研究戏曲成了我的“专业”,我在守候母亲临终的病榻前头,历时三月,在后来补做的温、瑞、平三地田野调查及父亲平时记录的资料基础上,写成了长文《温州地方戏概观》。这就是后来(2005)收入我的台版文集《戏曲十论》中的《温州地方戏概论》,作为我对已经逝去的父母的永久纪念。
回杭州后,离开学还有些日子,我决定去一趟离杭州不远的长兴县。二妹秋姑和二妹夫的工作地点在长兴长广煤矿公司,去那儿既是探望他俩,也是为提前跟他俩告别。
二妹在煤矿电厂搞配电,二妹夫郑冷双在电厂任车间主任,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电厂在离长兴县城五里地的“五里桥”,没有职工宿舍,二妹两口子租住在厂附近的一间农舍房子。平民夫妻白手起家,大多如此。
二妹、二妹夫白天上班,我一人呆在农舍没事,也没有别的可去地方,正好用来读戏曲、做札记。我保留的写于1960年9月上旬的《关于两个本子的<白兔记>》、《关于<西游记杂剧>》等札记,都是那时候做的。前者还成了我21年后(1981)硕士学位论文《成化本<白兔记>艺术形态探索》部分内容的雏形。可见学问之道,在于长年的坚持与积累,跟“练兵千日,用于一时”一样道理。
二妹夫见我爱好戏曲,担心在农舍呆着无聊——其实才不无聊,便带我到城里戏院看了一场戏曲演出。好像是越剧,什么剧团、演的什么戏,全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和记忆了。在长兴那么小而偏僻的县城里,真的不太可能会有好的戏曲演出。
我的七个兄弟姐妹,这个进、那个出的,一直没有在家团聚生活的机会。唯一凑齐的一回,大概就是1995年春天父亲去世,我们七子女会齐给他送丧的那些天。期间曾留下这份值得纪念的合影照片——

我的七兄弟姐妹
(左起:老三秋姑,老六阿静,老大阿涛,老七光华,老二春姑,老四茶花,老五阿川)
大学最后学期,中文系状况发生较大转变。
反思前7个学期频繁搞运动,师生长期在外劳动锻炼,教学严重缩水,上课时间统计不足3个学期。主科“中国文学”即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课,有头没尾。“中国文学史”课根本没上。更滑稽的是,在停课搞“教改”期间,“教改”小组提出用《选集》作“古汉语”基本教材。理由是,《毛选》是“活学活用”古汉语的典范,不去研究典范,怎能使教学“古为今用”?于是发动大家去“挖掘”《毛选》引用的古文词句,像“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冒天下之大不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类成语、名句,就成了新编“古汉语”教材的常用句例。老教授们见了苦笑不得,但迫于形势,也只得说“这办法不错”。
为了弥补缺失,中文系来个矫枉过正,最末学期恶补专业课程。在古代文学方面,开了一门查漏补缺的功课:古典文学研究专题。杭大中文系尤其古典文学教师队伍的实力整齐,堪称全国高校一流。旧浙大文学院的教授大部还在,他们从先秦至近代文学,可以排出一连串的名师讲席。大四的这门“专题”课,由王焕镳讲先秦散文,夏承焘讲唐宋诗词,胡士莹讲小说,徐朔方讲戏曲,蒋祖怡讲古代文学批评,代表了当时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其中仅徐朔方为中年讲师,正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此外还有不久前刚离校的陆维钊(魏晋文学)、钱南扬(南戏)等老教授和正处“茁壮成长”的青年助教蔡义江(唐诗)、吴熊和(宋词)等,加上系主任姜亮夫教授(楚辞、敦煌文学等),可谓门道齐全,名师充沛。

夏承焘老师
这门课的学生课程代表仍由我担任。我课余接触最多的是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夏承焘教授,参加由他主持的教授、学生、领导“三结合”集体备课活动,领受了不少课堂之外的教益。这方面详情,我已写进了已发表的《夏承焘师二三事》等文,不再重复。
倏忽最末学期即将结束,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毕业去向。分配之前,人人写决心书,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些党团干部还表示要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国家形势仍不乐观,各地都在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大家对于去向,心理上都堆积着阴影。
分配方案迟迟没有消息。我就利用暑期等候毕业分配的时间,于8月8日,去了一趟上海六舅父家。六舅父在我母亲十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母亲是老八),年近40。到他出生的年月,族居诗情加富态的“大隐庐”的外祖父家,已经败得差不多。六舅父长大时,无力培养他多读书,就送他去学西装裁缝。后来六舅父到了上海,凭其心灵手巧,学得一手好手艺,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童装设计师。
头一回去上海,路不熟,我雇了一辆人力黄包车,让车从火车站蹬到六舅父童装厂所在的“四马路”(福州路)。路远车慢,正好供我一路观赏上海滩风光。
十里洋场,车水马龙,一路声喧。路过闹市之处,还能见到响着叮叮当当铃声的有轨电车。它使我联想起旧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故事发生的场景,还有茅盾小说《子夜》所写吴老太爷坐黄包车进城的情景。
离童装厂下班时间还早,六舅父让我先去“四马路”转转,“白相”一下。“四马路”是旧上海红粉世界、十里洋场的缩影。那儿洋楼林立,娱乐场所遍布,著名报馆、书局、书肆满街。走到一个路口,我居然见到了我心仪已久的“天蟾舞台”,异常兴奋,儿时父亲给我讲说的发生在那里的种种梨园盛事,好像都重现在眼前。
在上海逗留的日子里,半个京剧迷的六舅父,跟父亲一样,空时便跟我神聊海派京戏。被他赞美最多的,也是童芷苓,跟父亲“英雄所见略同”。
我到上海第二天,六舅父收工回到家,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梅兰芳昨天去世了!”
这个消息对我俩无异惊雷震地,六舅父大概是从上海电台或报纸最先得到的。看过梅兰芳演出的他,说这话时,是满脸的沮丧和痛惜,而我的最先感觉是:想看梅兰芳,今生休矣!
几十年后,我来到北京,供职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后身的戏曲研究所。每当我出入东四八条那座老院长开会、示范过的礼堂的时候,或带领友人参访护国寺梅家故居,跟梅氏男女公子梅葆玖、梅葆玥合影留念的时候,或在中国戏曲学院课后跟梅先生重孙、我的学生梅玮攀谈的时候,或在剧场与荧屏听到梅派徒子徒孙们无休止地重复《醉酒》、《别姬》等经典唱段的时候,都会不自禁地想起1961年8月8日,想到六舅父当时告知我梅大师去世消息时的那番惊悸和失落。
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六舅父带我去离住家人民路不远的上海黄金大戏院,看了一场上海京剧团的演出。这座由黄金荣1930年创办的近代著名剧场,见证了“四大名旦”及马、麒、谭、盖等大批京剧巨匠的风采。在我的感觉中,坐进剧场的意义,更重于看戏价值。
那晚买不到好票,座位落到了尽后排,看不清戏,也记不清演的戏名和演员名字,好像是“玉”字、“正”字辈演员,像李玉茹、侯玉兰、关正明、黄正勤等一批上海当红演员在演。这是我大学年代最早也是唯一一次在上海戏院看戏。
回到杭州学校,仍不见分配消息。大概在调整、精简年代,各处都不太需要大学生。等啊等,一直等到9月上旬,新学期已经开学,中文系新生也已报到,我们毕业生需搬离居住了四年的学生宿舍腾给新生。大家只好将个人行李打包,集中堆放在系办公室,自己随便找个办公室甚至教室空地打铺睡觉。大学结局如此凄凉,对比入学时的那番兴奋与期待,感到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伤感和失意。

毕业离校前,我们提早搬离了这座居住了四年的学生宿舍楼
(注:此楼后改做青年教师宿舍,今已拆除改建为教授楼“启真名苑”第一幢,照片采自薛家柱学长文《我在杭州大学》)
一天,系里突然通知,全体中文系毕业生集中校礼堂,宣布分配方案,并且决定当日即要离校。
礼堂鸦雀无声。大家个个竖起耳朵,细心捕捉几秒钟内决定的个人去向信息。当我听到我要回家乡温州地区的宣布,虽然还不明白具体地方、单位、职务,我在失意中却感到一丝的幸运。不管怎么说,我也比那些将要远离家乡的许多同学要幸运得多。
当日傍晚,我们坐进驶离省城的火车车厢。一起去温州地区报到的毕业生占了半节车厢,上海的,江苏的,安徽的,福建的,浙江各地的,温州各县的全有。浩浩荡荡,声势空前。在这之前,很少有杭大学生尤其外省市的学生分配温州的,这是精简、下放大潮的惠赐。大家带着说不清的各种滋味,踏上新的人生旅程,去迎接莫知的未来。
火车汽笛呜呜响起。
告别了,亲爱的母校。
告别了,尊敬的师长。
告别了,曾经笑语喁喁,絮言叨叨,甚或怒目灼灼的同窗好友们。
告别了,校园草木,古杭名胜,西湖风光,古旧书铺,快乐剧场……
列车慢慢驶离“城站”。“城站”是我四年前迎来大学生活的起点,又是我如今告别大学生活的终点。我的人生之旅,在这儿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圈。
四年轮回,照样的旅途,照样的行囊,照样的衣装,还有没机会穿过的衣衫的照样的旧摺,统统携带回家乡。行囊中多出的有:箱中几本专业图书,一些讲义,散杂笔记簿册和叠叠纸片,还有压在箱底的这张陪伴我今后50多年的毕业师生留影——

“杭大”毕业照
(本编涉及的照片中人名,说明如下:本人,四排左一;王继阳,二排左三;李广德,四排左六;顾志兴,四排右五;吴玉琴,二排右一;柯善才,二排左二;徐志行,二排右六;倪振庭,三排左三;李灿华,三排右二;叶金瓯,三排左六;蒋祖怡,一排右六;徐步奎﹝朔方﹞,一排左四)
【附录】
一个时代的戏场春秋——读《戏缘》杂感(苏泓月)
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戏缘——孙崇涛自述》读后(陈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