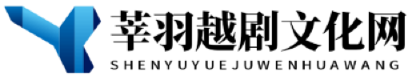到长安大戏院看诸暨市越剧团演出的《西施断缆》,观众极多,几近爆棚。我对越剧所知甚少,不清楚这是出老戏,还是新编,听唱词和伴奏,看背景与舞蹈,现代味很足,暗自猜想,会是越剧为迎合新时代的观众而作的努力吧? 历来对西施的传说和演绎不一,但有这样两点大致却是一致的:一为西施是中国有名的美女,二为西施在吴越之战中以身救国,换得弱小的越国的胜利。所谓的美人计之中,西施成为了令人赞美的美女兼英雄。中国的历史,一直处于男权统治下,在国与家、集体与个人、男人与女人的平衡系统和价值系统里,女人总是要成为最先的牺牲品。特别是在战乱之时,民族危亡时刻,极其愿意将女人推向第一线,而且还特别愿意用西施这样所谓的“身体”或“”,完成传统社会中对女人从红颜祸水到巾帼英雄的转换和塑造。 此次越剧《西施断缆》中的西施,很容易成为这样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演绎。这种演绎,几乎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种民间心理的认同,从来红颜多祸水,和自古巾帼出英雄,是垂挂在我们心头和潜意识里工整对仗的上下联。其中《西施断缆》中的“断缆”,不仅成为了全戏的,而且也把西施架在火上炙烤。炙烤出来的结果,是西施的贞洁烈女之心和貌似壮烈的悲剧,同时也是我们作为男权社会里所有他者的尴尬。 我想起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那里也有一个女主角,叫做佛莱莎,带着三个孩子。她同样出现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和我们这里惯常表现的不同的是,雨果没有让女人作为的牺牲祭品,而是让这个女人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出现在大火里,与反敌对双方的代表,三个男人为救她和三个孩子而进行了一场同意义同等重要的人性的选择,而不是让西施断缆而去,用我们自己的手,将女人送入敌手之中,送入大火之中。如此相比,我们对于西施似乎少了许多怜香惜玉,而显得无情,至少是尴尬。 有意思的是,此次诸暨市越剧团演出的西施,毫不掩饰地演绎了这种尴尬,并且不甘心这样的尴尬而力求新的出路,让他们的西施有一点别样的不同。在传统戏剧和民间传说的甄别筛选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仔细与用心,以及努力别出机杼的翻新。 在传统的吴越之战的演绎里,范蠡总是以正面主角出现的,他为国牺牲了自己所爱的女人,以及最后赢得胜利后带着心爱的女人一起功退归隐,泛舟湖去,形象高大动人,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原则和道德精神。这一次的范蠡却不尽相同,西施的表骂他负心而背叛爱情,虽显得多少有点现代,却表达出了他们对于西施所处男权社会所作牺牲的一种新的理解和诠释,是范蠡把西施一手从爱情的悬崖推入的漩涡,还要打着爱国的高尚旗号。西施便不像以往,只是面对红颜救国的一种选择,而多了另一种对于爱情的选择。于是,西施才多了面对范蠡失望后投江自尽的戏,使得戏多了以往戏里少有的人性的复杂与起伏,使得西施的形象更加丰满可爱。 戏的,范蠡紧追船只,拉住缆绳不放,显得有些矫情和做作,只是此时此刻的西施断缆而举身赴吴,让戏又过于轻而易举地落入老套,是此次越剧演绎努力突围中的落网,显示出他们和我们共有的尴尬。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此次西施断缆,不是一次突围中的落网,而是突围中的挣扎,可以看作既是对于以身许国的决绝,也是对爱情告别的决绝。西施的光彩,便不止于传统戏里爱国救国,而有了对男人苍白的爱情与男权顽固的社会的些许批判色彩,而使得戏的主题有了多义性。无疑,这是值得称道的。特别对于传统戏剧,面对继承与创新的双重考验,诸暨市越剧团为我们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和努力的奉献。而作为观众,遥远的西施和现代的我们,便能够彼此拉近,互为镜像。 (摘自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