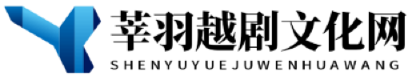自六月底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来京举行成立30年演出以来,今天是北青艺评第三次刊登关于茅威涛及其主演剧目的评论文章。
一部《二泉映月》、一部新版《梁祝》,引起如此热烈且褒贬各异的争论,这背后,除了对茅威涛一人、越剧一个剧种的关切,恐怕还有各位评家深藏于内的初心:在加速度前进的社会中找到立锥之地,是包括越剧在内的传统戏曲以及所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本土艺术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找到推动戏曲进步的根结,为缠绕多年的问题寻找答案:中国传统艺术的生长点和创造力是什么?下一步探索与创新的方向又在哪里?

在专家们欲语还休、点到为止,观众们随性吐槽的大环境中,茅威涛这样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能够在行业内外引发一些严肃思考后得来的客观之声,是我们此番最乐意看到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茅威涛们所从事的艺术创新实践,无论成败与否,都能看到中国人重拾文化自信、让东方审美重现光彩之艰难。
7月4日,我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对茅威涛新版《梁祝》过度唯美化追求倾向的批评文章,话说了很多,也谈到了我的审美观,以及评价的标准,话已说尽,原本不该再来解释。因为作为写文字的人,总是抱着“知者自然会知,不知者也未必一定要使之知晓”这样的理念。可是7月8日看到周黎明先生对于我的评论发出了他的商榷文章,从礼貌的角度着想,还是回复一下。

茅威涛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位演员和艺术家,20多年前我就看过她的戏。但这并不妨碍我独立的艺术批评。对一个作品的喜爱和一个人的喜爱,我从来不会放大到盲目的程度。在我的笔端,没有朋友,没有熟人,没有历史,没有奖项,没有哪个人,而只有她完成的艺术品的高低(事实上,我看《梁祝》的票正是茅威涛女士所赠)。
周黎明先生所言“评价茅威涛的艺术,必须要捕捉她的追求和轨迹,而不能用现成的框架来套用”,又说“茅威涛的艺术常识表现出一位成熟艺术家的眼光、胆识和高水准,评判者至少需要跟上她的步伐才能看清全貌”,我并不以为然。

每一个艺术家的每一个作品,自它诞生那日起,便没有前世今生,不论创作之辛苦、思考之多艰、视野之宽广、抱负之远大,而应只论这一个孤立的艺术作品的品格、风貌、趣味和美学价值。夏志清先生评论中国现代小说,否定老舍的《四世同堂》而认同《骆驼祥子》,不屑巴金的《家》、《春》、《秋》而单取《寒夜》。傅雷先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更说:“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我也如此认为,如果我没有看到过茅威涛其他作品中很美的一面,我绝不会来写之前的文字,也不会痛心、惋惜她被这个戏“吃掉”,消失了自己的美。
还有,我认为看艺术作品要看艺术品的“追求和轨迹”这样的话,绝不可以对买了票的观众去讲。“尽管我的作品是失败的,但是我的追求是好的。”这如同在公司打工而告诉老板说,虽然我没有完成既定目标,又花掉了你一个亿,但是我努力了,我有很好的追求。艺术批评不存在这样的标准,而隔靴搔痒的批评时代也应该尽快过去。

人们常叹品格的丧失,在评论界,正是丧失了“爱之深”,又丧失了“责之切”,更丧失了“评论家的孤高”。原本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原本艺术评论家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品格、高超的审美胆识和勇敢的铁口直断,可现在太多温吞水、中庸主义、哼哼唧唧的文章和作品研讨会,左抹一下,右拉一把。作为欣赏艺术的常人,要求他在艺术品鉴面前六亲不认,这当然是苛求,可艺术评论家,握着如椽巨笔,自当知道什么是一字千钧。我很赞赏周黎明先生在《看电影》专栏中的一些长文,因此我觉得您应该和我有一样的认知。
在戏曲评论的层面,也向来存在着两种滑稽又感性矛盾的观点,一种是“戏曲创新即错”,一种是“遵循传统即错”。其实都不对。我在前文已经表明,我反对的并非是茅威涛的创新,而是创新的质量。我反对的也不是唯美,而是美的质量。梅兰芳先生的“移步不换形”,齐如山先生不同意把戏曲舞台上的舞器“切末”称为话剧里的“道具”,皆是从深谙戏曲美学的角度出发,再来谈创新。

从中国土地上长出来一颗土豆,并不因为包上了一层粉紫色绉纱纸,配了三把满天星,又用喷壶喷了一些晶莹的水珠,就成为玫瑰。不过,如果你要把这个土豆做成薯条,我并不反对,但是你也应先找到土豆的本味,再买一个烤箱和一瓶番茄酱才对吧。
新《梁祝》,我只觉得它是歌舞和形式主义的嫁接,是以牺牲越剧本身美的基因,牺牲艺术创作中必须以人物为中心的原则,进行的空洞和表面化的创作。这就像领袖带着学者上了城楼,指着偌大的北京城说,看见了吗,以后从这里望出去,要处处是烟囱——有那种透心凉!
它的唯美也是晚会式唯美。新《梁祝》的集体扇子舞,如同张火丁和张春华先生的神品《秋江》上了春晚,前面出来一批孩子在那里兴奋地划桨,这样的尝试与其说是勇敢和创新,不如说是格调不高的败兴和滥情。
周黎明先生开篇即以《如梦之梦》、《尼伯龙根的指环》来反驳我说的新《梁祝》蝴蝶意向的过度使用导致的笨拙和累赘,先不说作品的不同,单说理解的程度,已经明显是误解我说的“简明”之意,认为少用几次蝴蝶,即是我认为的“简明”。这就狭隘化了我的前后文意思,并且没有看清我说它“不顾合理性去屈就蝴蝶”的段落,显然也没注意到“草蛇灰线”那段。至于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反哺”《梁祝》之事,也幸亏周先生提醒,在前文是我遗漏未说之处。周先生赞扬这种使用,我也非常反对。
从音乐本身的品格和传递的情绪来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它的气味、颜色和感彩,它惆怅、缠绵到不可挽救,它是极致的,不适合用在剧情之中,当然更不适合在剧情中一再出现。正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阿炳的《二泉映月》,一个悲壮艰难,一个宛如叹息,乐曲一响,情感即到。在新《梁祝》中提前使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而不是化蝶的末尾,那么它只会把那一折塑造的情绪和演员表演吞掉,置换成它的情绪,由它来表演。而此时这种表演突兀和剧透,就是浮夸的风和没有根的草。
伟大的德国批评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妩媚出现在不恰当的地方,便是矫揉造作,便是丑态毕露;同样的妩媚,如果反复出现,也会遭到冷遇,最终将令人讨厌。如果演员以在法国式的三步舞会上用的手势来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或者他的道德说教像纺车的捻干一样重复出现,我会认为是小学生在念儿歌。”
周先生又以黑泽明来比较我说的小津安二郎,说“小津固然是非常高的境界”,但黑泽明一定不合“我”口味,因为他的电影美学很“重口味”——这又是另一层的强行判断。因为“简明”在我的美学观中,并不仅仅是指风格,而是指境界。小津安二郎、阿巴斯这一类固然是“简明”,黑泽明、沟口健二、安东尼奥尼、安哲罗普洛斯、拉·斯·冯提尔、希区柯克、是枝裕和、昆汀·塔伦蒂诺、李安、王家卫的第一流作品亦都是“简明”。正如我说,“不惟《诗经》是诗,《左传》亦是诗”。
黑泽明的《七武士》、《蜘蛛巢城》、《罗生门》、《生之欲》、《梦》,那种节奏、情绪、人物、画面的控制以及传递过来的力量,最终到达的高度,何其“简明”也!而且我原文里说的本来就是:“艺术是有普遍规律和终极审美的,无论它的过程多么诡异、个性、泼辣、繁琐,无论它是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它是传统还是现代……”。
要知道,我认为的“简明”是一种禅境,是所有不分门类的第一流艺术品都会到达的超凡境界。是哲学的,亦是美学的。那也是当我们作为欣赏者,看到一件艺术作品时,感受到的它的不可思议和无法理喻。它是绚烂之极归于的平淡,是旧小说《水浒传》里陆谦着人穿旧衣衫站在桥头向林冲卖刀,也是《金瓶梅》里西门庆让宋惠莲去换一条翠蓝色的裙子配她的红袄,更是《西游记》里唐僧到达极乐世界,坐着无底船看见自己的肉身顺流而下时,孙悟空笑着祝贺他终于“脱胎换骨”——是那样地百转千回、前赴后继之后,“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除此之外,中国艺术乃至世界艺术,再没有另外一个至境。
周黎明先生还提到了“文人美学”的概念,但是周先生显然没看过《陆游与唐琬》,那一种舞台美术才是我欣赏的文人美学。戏曲表演中,说人的动作很“脏”,以及艺术鉴赏里,说一个艺术作品的气质很“脏”,也是说它有很多的多余。《新梁祝》就存在这样的多余和不“简明”。它就是那沉重的、飞升不了的肉身和宋惠莲配了红袄的紫裙。
昨夜看高居翰《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正好看来一句话,可与周先生同观。第二页的第三段:“诗意画在中国刚出现时,更多是被辨识和体验出来的,而不是被有意创造出来的。”所以,当越剧新《梁祝》有意创造和改造越剧,却忽视了戏曲本身的趣味、基因、写意的美、角儿的个体的时候,无论它多努力,用了多少机关和舞美,也只能是一条唯美的歧路。当剧终化蝶时,粉红色的蛱蝶在坑道中被鼓风机吹起,美则美矣,余味又有多少呢?
戏曲创新的道路走了几十年,作品可谓车装船载,花费无数,然几无成功之作,批评环境不够良性,也是病灶之一。我是一个作者,我会把莱辛的另一句话当做我写艺术评论必须秉持独立品格和趣味的激励。他说:“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有人曾经断定,我那直言不讳的评论会激起许多读者的愤慨。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点有限的自由(这可绝对不是什么区区小事),我将冒险使他们常常感到愤慨。”
也把这句话送给同为文艺评论人的周黎明先生共勉。
【观点回放】 张敞
新版《梁祝》在创新时,还有一种误区,其实这也几乎是所有戏曲创新的误区。那就是它似乎认为把戏曲做得时尚就可以吸引年轻人,因此花哨炫目,因此声光电,因此中国古典舞加后现代剧场艺术,因此紧跟流行。可惜,这种逻辑根本就是错的。首先,这些手段不是“时尚”,而是“时尚”的反面——是一种土气。真正高级的时尚是从容的、平和的、低调的、走入内心的。它们太喧闹了,太一眼可以看到底。
我粗略数了一下,蝴蝶作为意象和实体出现了6次,书生群舞出现了3次,梁山伯和祝英台一起的扇子舞出现了4次。这不是反复咏叹,这是累赘和重复,当年王羲之写《兰亭集序》,二十一个“之”字无一相同。《梁祝》却让个人消失而变为广场舞。
片面地追求唯美而丧失美,刻意地追求诗意而堕入笨重,嫁接一般地追求“后戏剧剧场”那种文本靠边,舞美、化妆、导演的价值过度体现的方法,而最终令人出戏……若说张火丁版本的京剧《梁祝》生硬、干瘪、粗疏,茅威涛版本的新版《梁祝》则存在这样食而不化、审美格调不高、加法过多而不够简明的问题。
周黎明
张文评判茅威涛版《梁祝》,采用了一个既定的标准,即该文一开始提及的小津安二郎的例子。我承认,那代表着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艺术已臻化境后的简洁与平淡。但我们不能用这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艺术作品。假设你用小津来套黑泽明,会得出太过“重口味”的结论;反过来,你若用黑泽明的艺术来套小津,恐怕也会感叹“味同嚼蜡”。
用“时尚化”或“唯美”来理解这种创新,其实是褊狭的。首先,茅威涛和她的团队大大拓宽了越剧的外延,丰富了越剧的音乐语汇和舞台呈现。
茅威涛的艺术尝试表现出一位成熟艺术家的眼光、胆识和高水准,评判者至少需要跟上她的步伐才可能看清全貌,而用一个定点光来扫射则不利于看清她究竟走了多高多远。
茅威涛回应
一切理性的,就戏论戏的,非人身攻击的戏评;激赏勉励的褒奖或善意智慧的忠告,它会成为辅正你前行路两旁的参照树。那么,有什么理由拒绝?不接受呢?倒是当事者(评与被评者)千万警惕,不为溢美之词而迷失,不因无良言语而激怒。
网友热议
@发乎情止乎非礼:北青艺评又选用了张敞老师的戏评,窃以为写得大好,并未偏颇到哪里去,也不能拿着梅老板的创新来枉比,字间可见可嗅可触作者对于戏曲的不夹杂功利的玉壶冰心,也是刻厚(“尖刻而厚道”)的表现。
@水冰狐:作者单独不喜欢张敞提出具体意向过多的观点,然后他就说具体意向在其他文艺作品里其实很多的,逻辑对不上啊。不过这文有一个角度我是认可的,就是茅威涛对美的各种创新和尝试,这个戏也是一种尝试,不能盖棺论定。
@F:不能要求大家做艺术家的跟屁虫啊,要做对话者。
@TS:几年前在绍兴看过新梁祝,真心不喜欢。导演没才气,食新不化。满台的花招,糟蹋了好角儿。当时的感受是,要看这种花活儿,看越剧干嘛。
@DD:看一些新编戏会感觉艺术家的“身边人”不行,没有齐如山、罗瘿公、翁偶虹那样的高人了。
@临江望竹:一直觉得浙百是异常出色的剧团,从以前到现在没变过看法,所以有时看到缺点也难免会说上几句。因寄予希望,故要求更多。梁祝的本子是有点问题,但综合来看这个戏又异常成功,它成功地将作品与市场完美接通,审美上更趋同大众。有批评声不可怕,甚至该喜,戏曲团体最怕寂寂无声,那代表无人关注。张敞指出的剧本上某些问题是客观有的,这部分是可以改进的,稍微动几下就可以将这个戏再提高一个层次。而他提及的舞美舞台则牵扯到大众审美、市场考量问题,前后两处批评应有区分。作者很用心在写,看得出出发点是希望浙百更好。茅老师海纳百川有胸襟,难能可贵。
@ 田雨风鸣:有评点的人生才精彩,被关注的人生才鲜艳。
@小碗小碗小小碗:挑毛病永远比实践容易,当局者往往会受自身既定思维圈束。茅大近年的戏之所以能引起各种褒贬讨论恰说明她是成功的,她的越剧,她的出品,有资可谈,有味可品。世上本无真正完美的存在,越剧没有,茅大也不是完人,所以我们才关注。批评和表扬某种程度上都是喜欢。
@丫头_:点评向来都是个人化的亲。个人审美爱好的感受不同,当然结论就会出现分歧。支持戏剧评论真诚亮剑的心意,只要是不涉及人身攻击的,都应该感谢笔者的用心,态度见高度。喜欢评论者的用心点评,赞扬受评者的胸怀大度,这样相互理解的气氛下,让这一场喧嚣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摘自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