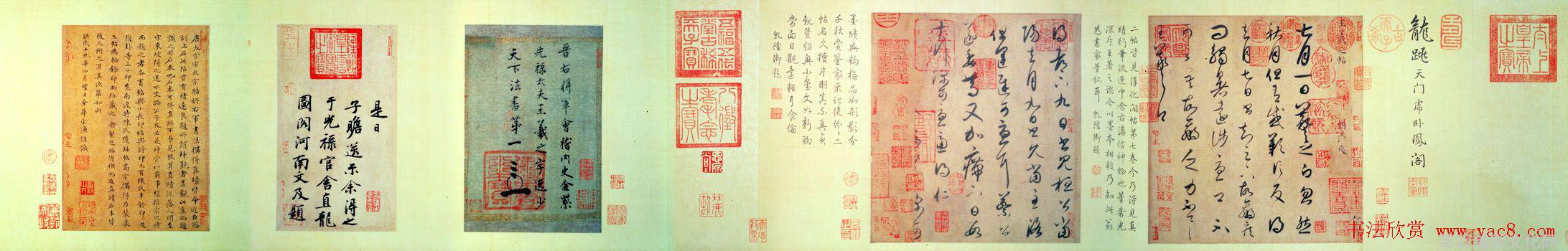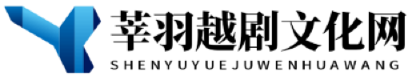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建团30年,恰好剧团来北京演出新《梁祝》,引起的反响大多在预料之中,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张敞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评论,还有周黎明针对张敞的批评写的商榷文章,然后就是微博微信上一系列热烈的、观点迥异的讨论。文艺评论版的编辑们希望我针对这些讨论说点什么,我是很想就茅威涛这些年的创作与演出写点什么的,多年没有写,是不知道究竟什么时间写比较合适。想到老家一句俗话,拣日不如撞日,于是就写在这里。
茅威涛在20世纪80年代初走上从艺道路,在初组建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第一部代表剧目《五女拜寿》中,她扮演的角色并不太重要,然而她的一段尹派风格鲜明的“奉汤”,却成为戏迷中传播范围最广的唱段。在以后的岁月里,她用自己的表演才华征服了观众,自然成为众星璀璨的小百花的领军人物,把小百花带入了全盛时代。浙江小百花是由一群艺龄不长的小姑娘组成的越剧团,她们可以在这个越剧各流派的创始人——“十姐妹”都还齐刷刷地健在的年头,得到观众充分肯定,其影响与地位不输于任何一家越剧团,无疑,功劳首先要记在茅威涛头上。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确切地说,就是从茅威涛决定创作新剧目《寒情》时起,她的艺术道路出现了根本转折。在这之后的一系列新剧目,从《孔乙己》、《藏书之家》和新《梁祝》直到更近的《江南好人》,她逐渐成为一个越剧界的争议人物。诸多的争议中,茅威涛当然是说过一些不够深思熟虑的话的,得罪了部分戏迷,也得罪了某些越剧界的前辈。其实不冷静的绝不止于茅威涛——当然你不能责怪观众们说的可能更过分的话,那是观众的权利,至于戏迷,迷谁和不迷谁更是他们的权利。只不过业内人士不难分辨,对茅威涛的那些比较尖锐和刻薄的批评,背后隐约还有那些感觉被她得罪了的前辈的身影。不过,这也不足为奇。
重点在于各种相关的争议,它们与茅威涛创作演出的那些不仅与传统越剧风格样貌迥异,甚至也与茅威涛得以成名的那些新创剧目有明显差异的表演,简直形影不离。有时我甚至觉得茅威涛自己也很享受这些争议,无论如何,它们让越剧始终保持了很高的大众媒体关注度,除了京剧和2001年之后的昆曲,越剧之所以能成为戏曲界最受关注的剧种,多少要拜茅威涛所赐。而且,由于有这样的高关注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越剧新剧目创作,包括上海越剧院那些和茅威涛同龄的优秀演员在内,无论她们是否自觉,无论她们是否承认,都不同程度地受茅威涛很深的影响。如此之多的争论并不全是好事,所以我在纪念浙江小百花成立30年的座谈会上说,茅威涛创作演出这些剧目,对她个人是一场豪赌,她是在赌越剧的当代影响和历史发展,而押上的赌注,是她的艺术声誉。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艺术领域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对各类艺术争议无保留的肯定,甚至简单地把“引起争论”看成是作品艺术价值的标志,然而,经常让自己处于争论漩涡中央,包含了巨大的艺术风险。就茅威涛而言,这些争议固然给她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对她造成的伤害,却也不能轻视。我总是以为,即使是艺术的争论,也并非全无是非可言,如果争论的一方最终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一点也不值得羡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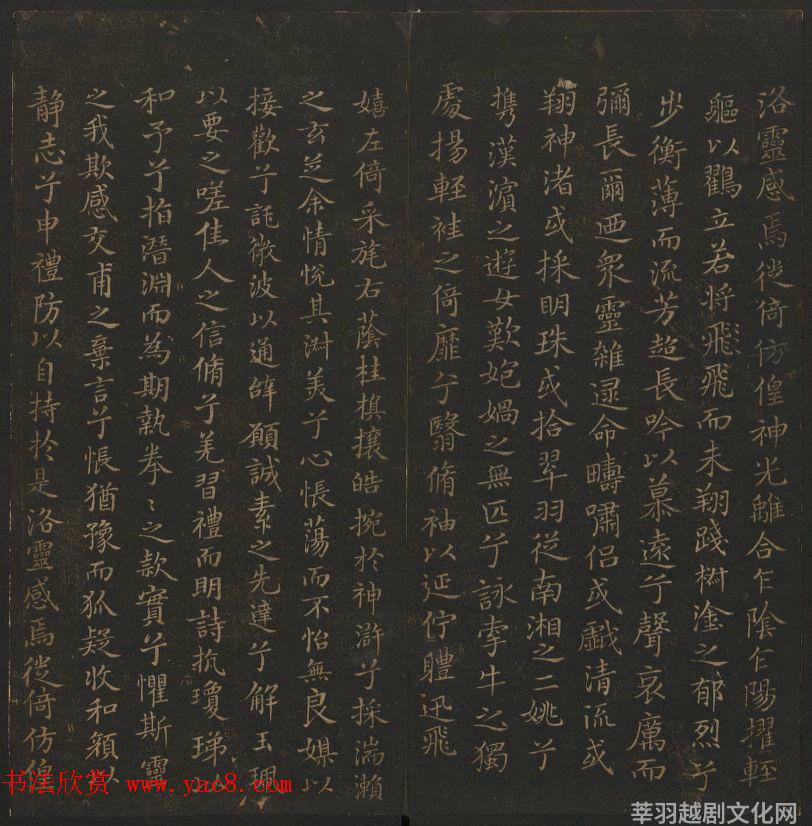
其实,我还有两个基本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评价一部戏曲作品可以有两个维度,其一是把作品看成一个独立的文本,孤立地从它舞台的呈现给予评价,其二是把作品放到剧种的框架中加以评价。如果从第一个维度看,我对茅威涛的那些新作,多数都有很高的评价。尽管这些作品的剧本,除了《孔乙己》之外,文学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但是茅威涛的个人表演能力,足以弥补其短;我甚至觉得茅威涛在《江南好人》中如此出色地扮演了女性戏剧人物,说明她的表演还有更多开拓空间。然而,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越剧的框架内加以评价,结论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诚然,越剧的传统并不完整,可拓展的空间还很多,不过对越剧自身的表现力的拓展,与逸出越剧的改造,完全不是一回事。茅威涛基本被引入了后一条道路,所以习惯了传统越剧的观众会逐渐疏离浙江小百花,这一点也不奇怪。至于因媒体大量的报道而好奇地进入剧场,并且喜欢上茅威涛的观众们,他们真的能成为新时代的“越剧观众”吗?如果他们只是茅威涛的观众,而不能成为越剧的观众,那么于越剧何益?因此,我从不反对艺术家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创造,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最低限度,就算为他们自得其乐,也已经是充足的理由。我所不能同意的,是简单地把自己的个人选择,看成是艺术发展的方向。我赞成并欣赏茅威涛自己的追求,包括她出演电视剧《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然而,我并不认为必须把这意义放大为越剧发展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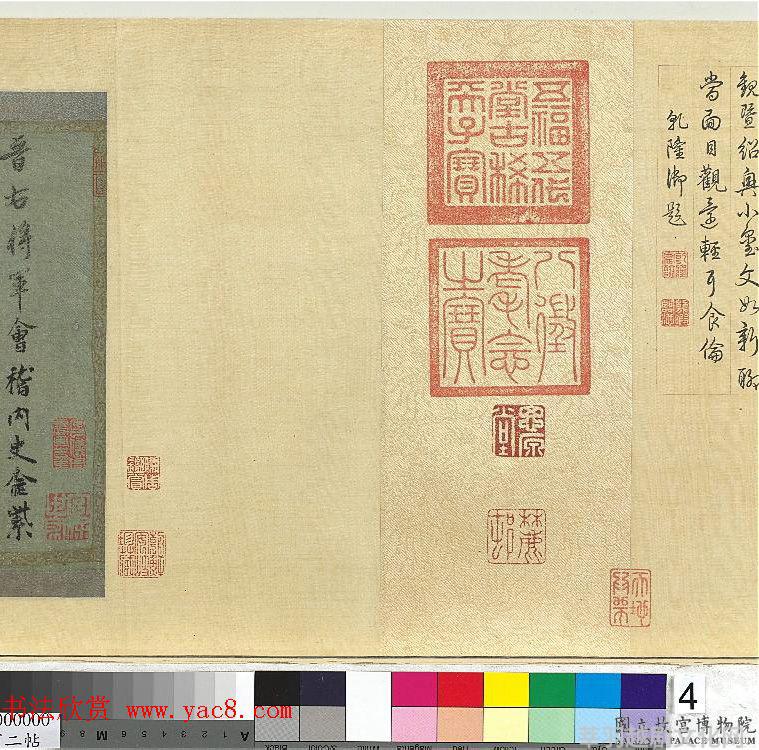
其次,我一直期待越剧,尤其是越剧中最具魅力的尹派表演艺术,其中又主要是其唱腔,能有好的当代传承。在戏曲艺术的范畴内,实际上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继承传统从来就不是一件坏事。有时我甚至想,我对茅威涛最大的期待,不是她演出一些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新剧目,是她能够把尹派名剧《何文秀》和《沙漠王子》唱得比尹桂芳更好。所以我为茅威涛的新作《二泉映月》的唱腔中尹派韵味更浓而欣喜。而像越剧尹派这样有人文深度的唱腔,是需要一代优秀演员才能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这个时代的越剧演员,能够实现这样目标的人,实在并不多。在我看来,这才是对越剧更具实际意义的继承与发展,我甚至幻想着茅威涛能够步余叔岩的后尘,当年余叔岩就是一门心思向谭鑫培学习,才成就他自己的余派的。茅威涛的聪慧以及她的好学,在众多的戏曲演员里少有可堪比拟者;她更有为越剧振兴且发展的自觉担当。因此她有今天的成就,或还可有更大的成就。从公而言,她似乎一直认为,只有不断地逸出传统越剧的格范才有可能实现她振兴甚至拯救越剧这一目标;从私而言,我当然清楚茅威涛希望成就自己的流派。然而,余叔岩的范本在前,岂非是一条康庄大道?
最后,有一个我始终难以解开的困惑:从《寒情》直到今天,茅威涛的那些新创剧目之吸引观众的理由,始终是、且只是茅威涛的表演。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是因编剧和导演的魅力而进入剧场,更不明白是否有观众因受舞台美术的吸引而去看浙江小百花的新剧目。通俗地说,浙江小百花直到今天,“卖”的还主要是茅威涛的表演。其他那些元素,某些给演出加了分,某些给演出减了分,两相抵扣,剩下仍魅力不减的,就是茅威涛。那么,茅威涛为什么还要背负那些无谓的争论?只要茅威涛潜下心来,她对越剧所能够做的贡献,实无可限量;而以她目前的影响力,让越剧重光,绝非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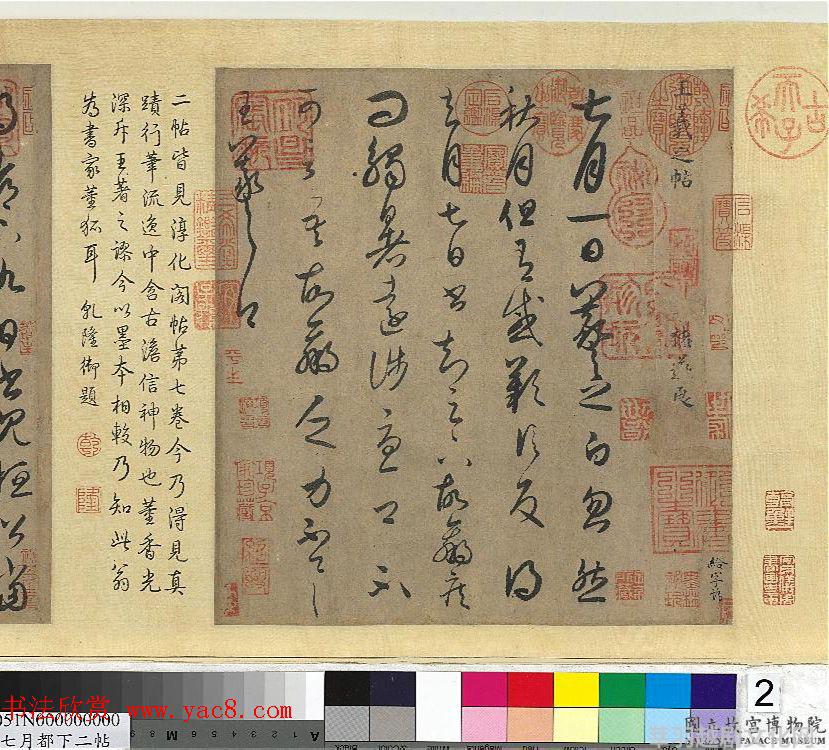
明明有坦途,然而茅威涛选择了崎岖。她的勇气,却未必走向光明。我努力理解茅威涛,然而,理解与认同之间,不是简单的等号。
(摘自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