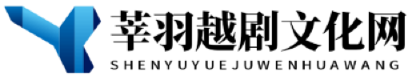越剧《西厢记·琴心》是袁派唱腔的经典,莺莺从红娘“小姐,你试猜呀!”起板,开头四句这般唱来:“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莫不是风吹铁马檐前动,莫不是那梵王宫殿夜鸣钟?” 莺莺隔墙听音,猜了四次不中,最后听清是张生的琴,更听懂了张生的心:“他曲未终,我意已通,分明是伯劳飞燕各西东。感怀一曲断肠夜,知音千古此心同,尽在不言中。”唱词来自七百多年前王实甫的原作,但作了删削调整,既简洁明快又不稍减诗情曲韵。《西厢记》是第六才子书,曾让黛玉读得目不转睛、爱不释手。但一般人若仅靠阅读,未必有她那般心醉神驰。正是那质朴细腻、含蓄醇浓的袁派唱腔,使黛玉的心头爱,成了妇孺的流行调。1943年袁雪芬在演《香妃》时首创了“尺调”,这种唱腔,好比京剧“二黄”,最能描摹出人物深沉微妙的心境,于是很快成为越剧的新主腔,融入各个流派之中;袁派唱腔本身,更孕育出了好几个新的流派。故此有位业内行家评说:“这一个调的出现,发展了一个剧种。” 一个浙东剡溪的小唱小戏,剧情简陋,唱腔单调,伴奏乐器仅为一鼓一板,相击发出“的笃、的笃”之声。但就是这个“的笃班”,在进入上海短短二十年间,却将才子佳人戏,演得流光溢彩兮。期间正是昆曲式微之时,袁雪芬却从昆曲的残红碎绿中,采得了越剧的春花秋叶。她请来昆曲名家饰腔正音、编舞配曲,使越剧的表演渐趋规范,格调渐趋清新,品位渐趋雅致,终于脱胎换骨、破茧成蝶,风靡上海以及整个江南。 与大多数为贫穷所迫的姐妹们不同,袁雪芬的父亲是位私塾教师,家境尚可。但她在十一岁时便不告而别,开始了“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涯,临走只从家里拿了一把折扇。当时的决绝和此后的坚执似乎表明,她的此生就是为唱戏而来。学艺初成,袁雪芬先在杭州唱了两年,然后搭了乌篷船,来到大上海。彼时“越剧皇后”姚水娟的风光仍在,而袁雪芬就凭着与马樟花搭档的《梁祝哀史》,很快成了“越剧新后”。 但三年后,马樟花溘然去世。这个姑娘人称“闪电小生”,原意是她当年像闪电般的出名,却不料这也成了她闪电般消逝的谶语。 袁雪芬与其他姐妹一道开始了对越剧的改革。她邀请了话剧的编导,制定了演出的规范,改善了服装和舞美,更突破了越剧演绎才子佳人的定式,将《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上演。当遍体鳞伤的祥林嫂在风雪中蹒跚挣扎,唱出“我只有抬头问苍天”,问出“魂灵到底有没有”,二十四岁的袁雪芬不但打动了无数观众,更被文化界人士誉为越剧“新的记程碑”。越剧改革的成就,主要来自吸收昆曲和话剧的营养。从昆曲中,越剧承继了精致、高雅的唯美主义风格,从话剧中,越剧则吸收了写实、逼真的现实主义精神。两者在越剧的经典作品、经典唱段中融为一体,在《西厢记》这样的传统古典戏里,前者呈于外,后者则蕴于内;在《祥林嫂》那样的现实生活戏里则反之。 我曾多次造访过袁雪芬在淮海路新康花园的寓所。八旬高龄的老人对我这个不惑盛年,迎必亲为开门、送必亲至楼下。她思路清晰、记性良好,一口“嵊县官话”话锋到处,往事犹如被剖开的新橙,逐一鲜明起来。她常忆起马樟花,说她若非含恨早逝,当年的越剧改革很可能出现别样的境界。她常忆起《山河恋》,说那次“十姐妹”义演,目的就是摆脱盘剥、争取艺术与经济的双重自由。她常提及自己的徒弟,说自己收徒不多,一是因人才难得,二是为精心教导。她常提及自己的座右铭,那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她谈得最多的是越剧如今又遇困境,新戏乏善可陈,流派停滞不前,人才青黄不接,因此越剧一次改革不够,还须改革、不断地改革…… 听着听着,一阕《水调歌头》渐在我脑中成形—— 剡水出伶女,的笃趁乌篷。小歌难唱还唱,只为此情钟。遍走繁华洋场,忍看凋零姊妹,电闪逝无踪。半掩英台泪,新后正当红。 香妃恨,山河恋,尺腔宗。幕开新纪,抬手擎杖问苍穹。心胜男儿刚烈,人比雪花清白,见说已消融。侧耳听春水,环佩响叮咚。 艺途犹如一条蜿蜒的水路,曲折地通向文化、通向哲学的巅峰。当走通这条水路,一个艺术家便能成为一代大师——这与文化素养有关,但更与道德素质、文化自觉有关。袁雪芬完成了艺术层面的超越,上升到了文化和哲学的层面,因此她的艺术精髓足以启迪后人、昭示未来。白雪虽已消融,却化作了叮咚流淌的春水。 我的内心试着扮演起莺莺,为的是试猜那如环佩、如春水般的声音——这是越剧未来应有的声音。
(摘自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