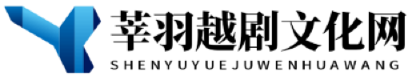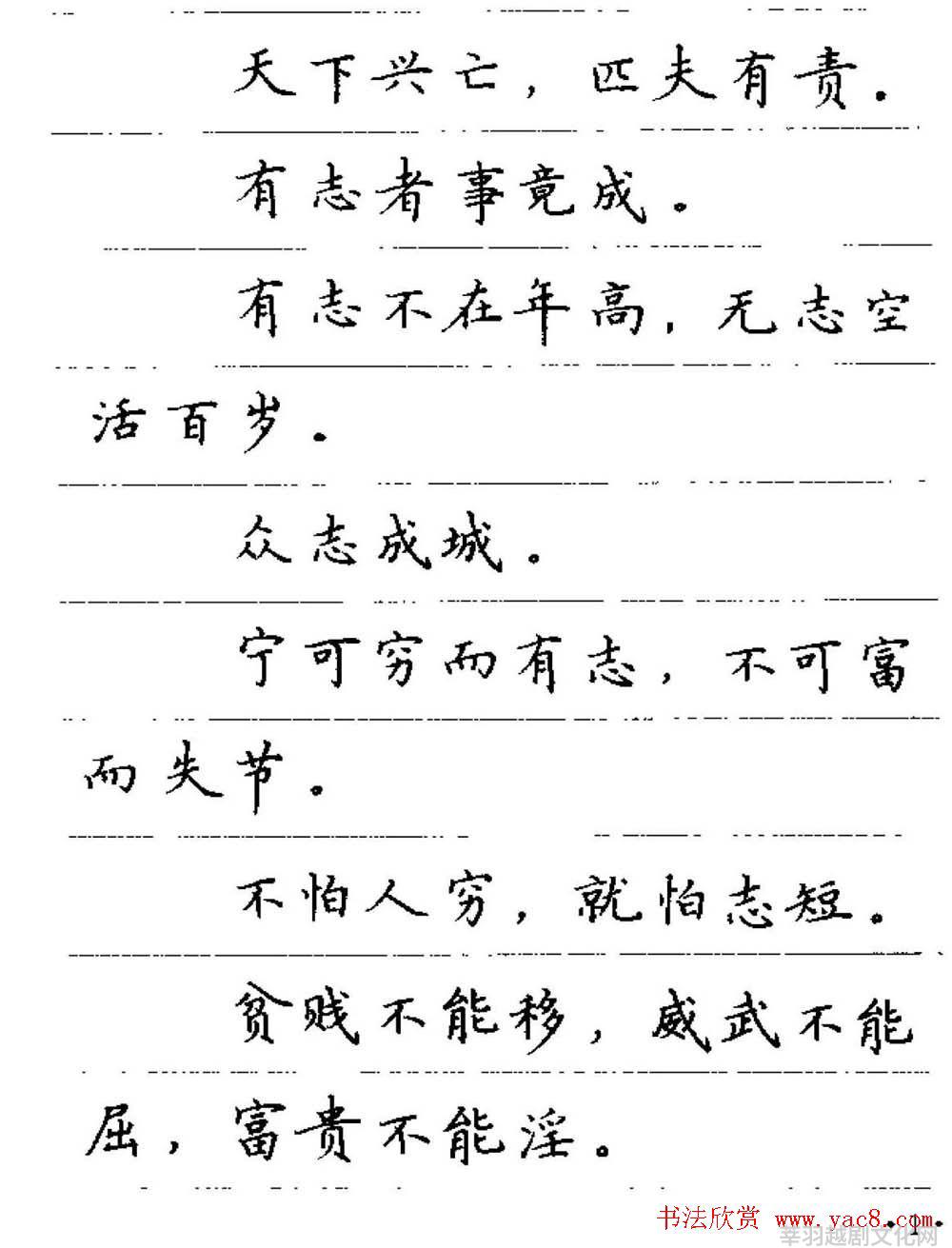《北京青年报》7月4日刊登的“新版《梁祝》误入唯美歧途”一文,对这部茅威涛主演的越剧提出了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蝴蝶这个主题意象的多次出现。文章作者张敞观剧时特意数了一下,共有13次之多,于是认为是“累赘和重复”。
在笔者看来,主题意象在一部剧中的出现次数和频率,是不应该被量化的。契诃夫的《海鸥》中,“海鸥”出现了不足三次,且十分隐晦;而《如梦之梦》一上来就讲了一大段梦。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之《齐格弗里德》中,那把剑来来回回提了无数次,这还没算作曲家在音符中潜藏的音乐形象哩。就说蝴蝶,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歌词里仅点题性带过,完全符合张文的“简明”,但某些经典舞台演绎里被导演新增了不少蝴蝶的影子,如巧巧桑临死时双臂晃动,做出蝴蝶扑闪的效果。你可以认为那是画蛇添足,也可以认为是点睛之笔,完全视自己的美学立场而异,很难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

张文评判茅威涛版《梁祝》,采用了一个既定的标准,即该文一开始提及的小津安二郎的例子。我承认,那代表着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艺术已臻化境后的简洁与平淡。但我们不能用这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艺术作品。假设你用小津来套黑泽明,会得出太过“重口味”的结论;反过来,你若用黑泽明的艺术来套小津,恐怕也会感叹“味同嚼蜡”。评价茅威涛的艺术,必须要捕捉到她的追求与轨迹,而不能用现成的框架来套用。再者,因为茅威涛探索不息,故评判者即便喜欢她某部作品,也不能全用那部作品来推及其余。
笔者有幸观赏了茅威涛《梁祝》、《江南好人》和《二泉映月》三部近作,诚然,这里面有导演郭小男以及其他创作人员的贡献,但应该可以确信最终效果是符合茅威涛的美学理念的。在笔者看来,茅威涛并非想做小津式的升华,中国传统戏曲原本就擅长写意,若要彻底“简明”,回归传统便是了。不夸张地说,去除所有舞美灯光等效果,甚至没有配戏的演员,她一个人绝对镇得住舞台,其他元素均是次要的。茅威涛想做的,显然是把越剧推进到当下,跟当下的观众尤其是都市年轻观众产生沟通,引发共鸣。

用“时尚化”或“唯美”来理解这种创新,其实是褊狭的。首先,茅威涛和她的团队大大拓宽了越剧的外延,丰富了越剧的音乐语汇和舞台呈现。《梁祝》里用源自越剧的小提琴协奏曲旋律来反哺,《江南好人》用评弹作为女主角以女性出场时的音乐动机,《二泉映月》当仁不让采用了无锡景,这种做法恐怕是纯粹派不屑也不敢做的。西洋歌剧也不乏外来旋律,如《图兰朵》里的“”和《蝴蝶夫人》里的美国国歌,但终究被改造成歌剧的表达,而茅威涛作品中这些外来因素却依然保留着原汁原味,同时又没有违和感,跟越剧的音乐相得益彰。这三部作品中最大胆要数《江南好人》,汲取各种中外表演艺术的养料最为驳杂,大概让以正宗为标杆的评判者很是不适,但它在嫁接西方音乐剧方面的成就恐怕也是最大的,让我们看到了戏曲创新的一条新路子。(当然不是必胜的路子,但起码是众多可能性之一)。
在舞台呈现上,《梁祝》和《二泉映月》都有中国文人美学的痕迹,这可能是让张敞老师误解的主要原因。相对于传统越剧,这种借鉴绝对是一大提升。这两个发生在江南的故事,摒弃了传统的手法以及49年后的写实,而是用了一种符合江南文人美学的写意,《梁祝》里仅有屋檐的布景和《二泉映月》里仅有椅子的房间,都是这个道理。主创大刀阔斧用了减法,但最终保留哪些元素,却不是按照某种公式计算出来的。因此,用以前的习惯来看书童扛不扛行李,实在是有点儿削足适履。如果说李翰祥电影版里他们必须扛行李,那么,茅威涛这版里扛了行李岂不是过于笨重,更不符合张文“简明”的旨意。茅威涛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有意识博采众长,接受古今中外各种艺术熏陶,她的创新是不拘一格的,我们只能评判某一部作品的风格是否统一。她的《梁祝》有自己的美学定位,所有处理均是从这个定位出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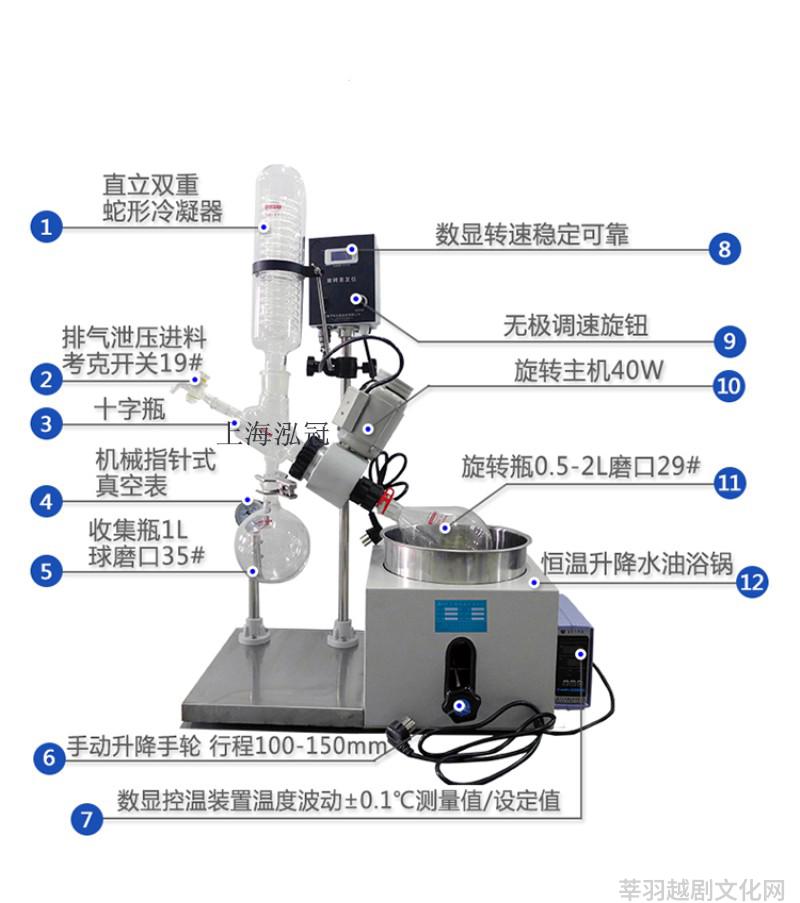
所谓“唯美”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茅威涛的作品跟文艺流派中王尔德那一派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小百花新编或新版越剧的舞台和音乐无疑都在追求美,但那只是众多美的风格中的一种,是相对比较符合当下观剧阶层审美观的一种。它文艺,但并不极致;它通俗,但并不流俗;它根植于传统越剧艺术,但又与时俱进寻求发展。这么说,并不表示这三部作品毫无瑕疵,譬如从我的角度《二泉映月》铺垫过长、对阿炳心魔的挖掘浅尝辄止,《梁祝》跟现代人的对话跟徐克版电影相比仍嫌保守,《江南好人》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不时显得啰唆。但毋庸置疑,茅威涛的艺术尝试表现出一位成熟艺术家的眼光、胆识和高水准,评判者至少需要跟上她的步伐才可能看清全貌,而用一个定点光来扫射则不利于看清她究竟走了多高多远。
(摘自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