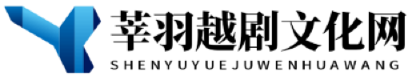此次采访,是在“活兰贞”的闺房里进行的。
不过,这位“大家闺秀”的生活相当节俭,房间里只有写字台、梳妆台几样古朴的家具。
只有床头挂着的《盘夫索夫》的剧照,透露女主人曾经红极一时的身份与地位。
金采风是越剧“金派”创始人,她主演的《盘夫索夫》、《碧玉簪》等众多剧目,已经成为越剧艺术的经典;她所塑造的严兰贞、李秀英等艺术形象,被誉为“活兰贞”、“神秀英”。
眼前的金采风已经82岁高龄了,但嗓子依然响亮,比个兰花指,模样俏得很。提到越剧,就越发神采飞扬了。
记者去的时候,客厅里放着两个大箱子,敞开着,里面全是各种制作精美的珠钗、头饰,“这几天天气好,拿出来晒晒,不然会坏的。”
尽管已经许久没有登上越剧舞台,但金采风还是很爱这些伴随她一辈子的行头。金采风说,对戏曲演员来说,行头是天大的事。
料子、绣花、颜色的搭配……在那个年代,剧团都不管,都要自己动脑子折腾的,“每个戏最起码要6套行头,同一场戏不能穿一样的,观众记得很牢的。”
回忆起那三十多年的舞台生涯,金采风说,苦啊。学戏学到皮包骨,眼睛还充血生了麦粒肿。不过,“幸福”二字,才是她回忆的主旋律。因为,遇见了黄沙――她的爱人,也是著名戏剧导演。
在越剧界,他俩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有名的“越剧伉俪”。他们珠联璧合,在艺术和生活上朝夕相伴。
金采风说,黄沙在艺术上带给她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老伴毕生追求的“老戏一定要新演”。就是在老伴影响下,她才既尊重传统又不墨守成规。
而现在,黄沙已经不在了,金采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他搞一个个人艺术展。
“你就是唱戏不会忘记,其他都不晓得。”这是女儿对金采风的抱怨。
对金采风来说,越剧真的陪伴了她一生,是生命中不能抹去的痕迹。
殊不知,刚登台的金采风,哪怕是跑个龙套,只有一句唱词,她就慌得神都飞走了。
于是,她有了一条不同于他人的“电台成名”之路,直到有了那些个经典的“活兰贞”、“神秀英”。
从大导演小明星到恩爱伉俪,丈夫黄沙一直是金采风不曾忘记的思念。哪怕是出书,若不拉上黄沙先生,她便断然不肯。
(以下记者简称“记”,金采风简称“金”)
【梁祝】 电台成名
在所有老一辈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中,金采风的艺术道路是最与众不同的。
她既非科班出身,也没有进戏校专门训练过。她是唯一一个从纯粹的越剧爱好者,成长为一代越剧名家的演员。
记:听说您从小是个戏迷,看过很多名角的戏?
金:小时候,我常去马路对面的戏院看越剧。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邢竹琴……都是我迷恋的对象。
有一次看了《梁祝》,回到家里,脑子里满是小生花旦哥哥妹妹的动人情景,想啊想的,实在熬不住了,就拿起床单,披在身上,在我家那张雕花的红木床上,模仿着刚才看到的动作,像发疯似的,一个人唱了好一会儿。
记:后来您怎么会去学越剧的呢?
金: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发生了困难。15岁那年,我考进了雪声剧团越剧训练班,拜师学艺。
但是老师们为生活所迫,整日忙着排练演出,根本没时间辅导我,训练班开了几次课就停掉了。
后来,二十多个同学陆陆续续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留在剧团当龙套演员。给我们的报酬是在日夜场之间吃一顿 “堂中饭”,当时,我也动摇过,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记:一开始,您演的都是太监、士兵这些跑龙套的角色吗?
金:是啊,我天生胆子小,怕难为情,上了台,灯光一照,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连步子都迈不出去了。一旦要开口,哪怕只是一两句话也要了我的命。
记得头一次开口,演的是清装戏《月光曲》。
演出前我横背竖背,已经滚瓜烂熟了,可一出场,真见鬼,唱词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一句都记不得了。
我愣在台上,胡编了几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词……
还有一次,是演《女儿国》,我扮演向袁老师(袁雪芬)饰演的国王报告军情的小兵,虽然只有一句台词,我也不敢小看。
早也背,晚也背,走路背,吃饭背,连倒背也背得出来,这样肯定没有问题了吧。
可一上台,风风火火地喊了一声“报”,袁老师询问“所报何来”,我一面对她那严峻的目光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亏得袁老师舞台经验丰富,急中生智地马上朝我叱了声:“下去!”我也响亮地回了一声“喳”,逃到后台。
我这一声“喳”,后来成为大家打趣模仿的笑料。
记:所以你的成名特别不一样,是在电台里唱出名的?
金:早先上海有很多家电台,经常请演员去唱戏。我很喜欢电台,因为面对的只是一个话筒,但电台外面却有无数听众。所以,只要轮到我唱,唱什么我都愿意。
有时我还一人唱两个角色。譬如唱《梁祝》“楼台会”,我既学范瑞娟老师唱梁山伯,也学傅全香老师唱祝英台。听众打电话到电台问,播音员说是一个叫“金采风”的小姑娘唱的。
日子一久,他们就记住了“金采风”的名字,常常点名要我唱。
【红楼梦】 改工花旦
金采风那时特别用心,对许多重要场子的唱段一字一腔,一板一眼都记下来,回去后再一一记到自己的小唱本上。她常常一人唱几个角色,还可以同时兼唱8种流派。
最早唱小生的她,因为经常在电台“顶唱”逐渐崭露头角后,进入了东山越艺社改演旦角。
记:您刚开始是演小生的,后来怎么改了花旦?
金:因为我的身材比较高,面架比较大,所以刚进雪声剧团时,老师认为我唱小生比较合适。
当听众熟悉了电台上的金采风,也开始注意起舞台上的金采风。一看,是个高瘦个,演的又是男角,不舒服,不适应。
这时我已经在范瑞娟、傅全香老师的东山越艺社,观众纷纷写信给剧团,建议我唱花旦。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想唱花旦,我喜欢旦角戏。
不过,各个行当都是一个栗子顶一个壳的。恰好花旦张云霞要结婚了,就让我顶替了她的角色,观众反应也不错。后来,我又在《红楼梦》中担当了袭人一角。
自此,我从生角改旦角算是改定了。范老师说:“你人瘦,改花旦蛮好。”
记:改了花旦之后,行头怎么办?
金:傅全香老师特别热心,当时团里没有适合我穿的行头,我自己又做不起,傅老师看我的个子跟她差不多,便把她的私房行头借给我。
但我的个子比傅老师还要高一些,裙子系上去有点短,只好系低一点。我的脚也比傅老师大,彩鞋穿上去有点紧,脚痛得要命,只好忍一忍,熬一熬,穿了几次也穿松了。
记:一提到你,大家就想到“活兰贞”和“神秀英”。
金:什么“活兰贞”、“神秀英”,不过是角色比较对我的戏路,尤其是《碧玉簪》,似乎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连我的家人,比如我妹妹金采凌,也认为我《碧玉簪》演得最好,似乎我本人也有点像李秀英。
【芦花记】 “黄金”伉俪
已故著名戏剧导演黄沙是金采风的爱人, 《梁祝》、《西厢记》、《追鱼》、《碧玉簪》等经典剧目,均出自他手。金采风与黄沙相濡以沫的家庭与艺术生活经历,被许多人津津乐道。
记:您和黄沙先生怎么认识的?
金:我们相识时,他已经是一位在戏曲界颇有知名度的导演了,而我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演员,又是上下级关系,平时很少接触。
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蛮帅,蛮正派的。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穿得干干净净,袜子永远是白色的,对人也很和气,标准的绅士风度。
记:那什么时候开始有感情的?
金:在我们第一次合作排传统小戏《芦花记》的时候,当时我要演一个狠毒的继母,但我一点都没有感觉,他给了我很多建议。
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很聪明,有想法,而且还挺帅的,所以就对他很有好感。后来,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一起。
记:你们平时在一起聊的都是戏吧?
进:我们喜欢一起去看戏。吃夜宵的时候,就说这个戏怎么怎么样,睡觉的时候也讲。
遇到琢磨不准的角色,我会先唱给他听听,因为夫妻关系近,也好提意见,(我唱得)高了低了,好听不好听,他都会帮我指出来。
他一直追求“老戏新演”,他说哪怕一个动作,一个地位的改进,就是在变。老戏出新才能有生命力。
从一桌二椅发展到布景、服装改进等,只要不伤害传统,观众是会满意的。
记:现在的许多越剧也在尝试创新,你怎么看?
金:创新是好的,但我现在还是挺忧愁的,青年演员太多了。有多少青年演员愿意为越剧做到底,有多少人在练功?有多少人在努力?
我觉得搞艺术工作的人,一定要专心致志。我当年就是人家练一遍,我练一百遍,只有我喜欢我痴迷,才能做好艺术,演员,就是要有“痴”。(记者/南芳 通讯员/俞艳芩)
(摘自 《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