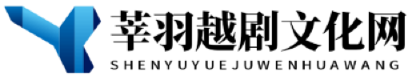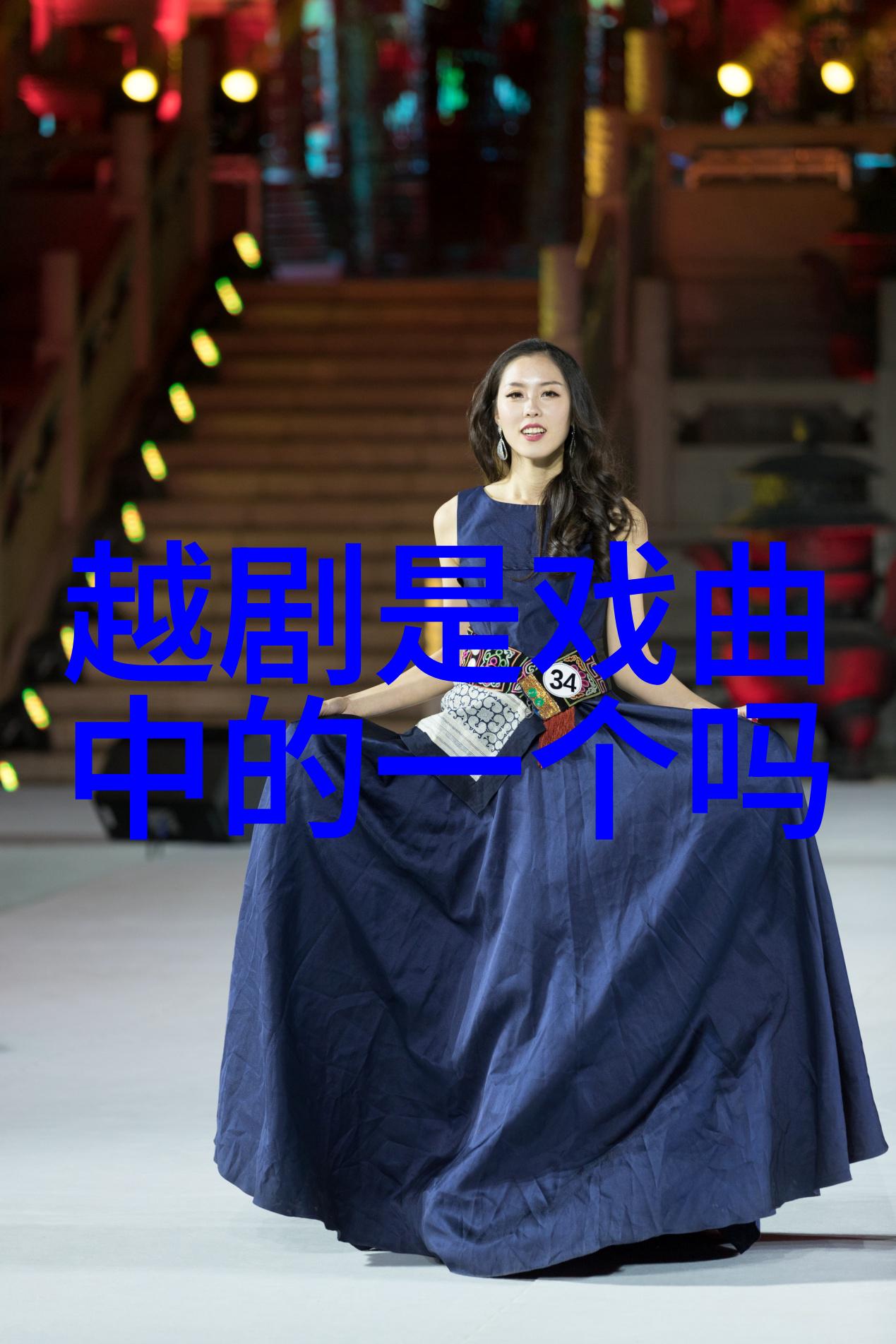龚和德
如果把越剧100年分作前后两个50年,各选一出越剧“第一代表作”,前50年,大家会选《梁山伯与祝英台》,后50年非《红楼梦》莫属。演出频率之高,社会影响之大,对越剧艺术品位的提升,对表演后续力量的引领,没有哪出戏可以超过《红楼梦》。
《红楼梦》的成功,证明并强化了越剧的相对优势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该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其一,明白晓畅,富于文采。如编剧徐进说,唱词“要一刹那就能抓住观众,引起共鸣”。同时,还要经得起观众的反复品味,这对于刻画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非常重要。因为这对“恋爱宝贝”是诗化了的生命,唱词要写得有灵气、富才情,才能不损害观众对他们的想象。如第一场《黛玉进府》,写宝玉眼中的黛玉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闲静犹似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拂柳”;写黛玉眼中的宝玉是“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恰切生动地表达了两人初见时的相互吸引。后面两句“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又照应了小说中的“前世宿缘”——实际上是一见钟情的传奇化而已。第十场《黛玉焚稿》,紧接林黛玉焚烧诗帕后唱的“万般恩情从此绝”,伴以幕后独唱“只落得一弯冷月葬诗魂”。这句唱词是从小说第76回林黛玉与史湘云中秋联句中的“冷月葬花魂”点化而来,剧作家把它移用在黛玉泪尽夭亡之际,把“花”改为“诗”,可谓一字之易,境界全出,一下子把大观园首席诗人凄凉逝去的景象升华到了诗的意境。其二,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据有的学者统计:小说中宝、黛吵架共有10次。这些争吵乃是爱情交流不可缺少的方式。剧中写得最有力度的是黛玉吃了闭门羹之后宝玉向她解释:“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初来到”一大段20多句,其中“谁知道妹妹心也大……也是个屈死鬼魂冤难告”,宝玉不知道黛玉为什么生气,饱尝了她的白眼、冷淡,心里万分委屈,仍然款语温言,向她作低、求恕,终于感动得黛玉淌下泪来,观众也随之潸然矣。又如宝玉在洞房中得知受了骗后,扑跪在贾母膝前说:“老祖宗,我要死了”,唱“我和妹妹都有病”一段,也是动人心弦的。其三,抒情性与戏剧性的统一。且不说《金玉良缘》一场由大喜转入大悲,只说《宝玉哭灵》。在小说里,黛玉死后,宝玉病了一场,后去潇湘馆“哭得死去活来”“气噎喉干”。徐进继承《英台哭灵》、《秦雪梅吊孝》之类民间戏曲传统,创造了这场抒情重头戏。宝玉从“金玉良缘将我骗”唱到“到如今,它果然逼你丧九泉”,共34句,有怀念、有自责、有控诉,悲情的宣泄是够充分的了,但这是生者向死者(灵位)的单向性倾诉,哪里去求得恋人黛玉的回应呢?妙在紫鹃在场,紫鹃是黛玉的知心婢女,黛玉是怀着对宝玉的误解和深深怨恨死去的,临死前直呼“宝玉!宝玉!你好……”紫鹃目睹一切,也深恨宝玉,所以,在这场戏里,紫鹃对宝玉的态度,客观上“代表”了黛玉。当紫鹃听了宝玉的哭诉,“心里已回过来些”,再等到宝玉问紫鹃:妹妹的诗稿、瑶琴、花锄、鹦哥今何在?两人对唱,一问一答之间,紫鹃的恨意渐为宝玉的真情所消融,在观众的想象中,也可以说,宝玉已取得了黛玉的宽谅。所以观众喜爱“四问紫鹃”,因为它既深化了抒情性,又增强了人物之间对立转化的戏剧性。最后宝玉唱“你已是质同冰雪离浊世,我岂能一股清流随俗波”,配以扔去通灵玉,响起远处寺院的钟声(这钟声,也可以理解为从宝玉的心灵中响起,是他出家之念已定的一种外化),为全剧做了很有“远景”也很有象征性的结束——宝玉要实现对黛玉的诺言:“你死了,我做和尚!”
从小说到越剧的形式转换,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创造,只有形式创造成功了,小说《红楼梦》里的人物命运及其精神蕴涵才真正成为观众以越剧样式来接受的审美内容。而剧本是基础,它的“上层建筑”,还有音乐、舞台美术以及舞台呈现的核心——演员表演。当那些优美的唱词变成了徐派、王派的经典唱腔,宝玉的柔情蜜意……黛玉的缠绵悱恻……被越剧“定格”,也才能使观众欣赏了近60年,传唱了近60年,感动了近60年!

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上海越剧院)《红楼梦》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