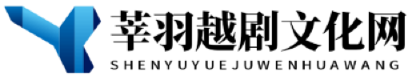越剧发展史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此之前,以男班为主的绍兴文戏经过艺人们不屈不挠的努力,正处于全盛时期,著名演员集中在上海;女子文戏蓬勃兴起,但活动地区主要在浙江,上海虽然也有女班演出,但多数带有流动性质,在整个上海的文化格局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甚至被人看不起。抗战爆发后,情况产生了明显变化,女班蜂拥来沪,迅速崛起,与此同时男班则急剧衰落,很快被女班所取代。越剧形成在我国独一无二的、以清一色女子演出为特色的剧种,几乎所有的著名演员、班社都集中到上海。从浙江农村、中小城镇来到中国第一大都市,要适应这里的环境、观众,以求立足、生存、发展,就不能不进行变革;而上海的社会、文化环境又为越剧艺术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越剧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孤岛的特殊环境。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就是历史上的八·一三事变。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最后一批中队于11月12日撤出上海。自此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年中,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被日伪势力包围的孤岛。租界外,苏锡文的大道市政府、梁鸿志的维新政和汪精卫的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相继登场。租界内,仍由英、美、法等国控制,倚靠着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互相利用和暂时妥协,与沦陷区及战乱不止的内地相比,局势相对安定。对内、对外交通畅通,内贸和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经济上出现畸形的繁荣。譬如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进出口商行从1937年的213户增加到1941年的613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几乎全从上海口岸输出。商业总户数、营业额和利润也都成倍增长。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无不迅速发展。
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越剧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是由于孤岛相对安定,大批外地人士涌入租界,躲避战乱。租界中的人口激增,其中江浙籍人士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部分人又多数从事工商业、金融业,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离乱的年代更喜欢乡音,地方戏的语言、音乐、反映的风土人情,容易唤起人们对家乡的亲切感情。绍兴八邑同乡会、宁波同乡会都曾为越剧戏班的引进、推荐越剧演员、组织越剧会串演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戏曲的发展离不开观众,地方戏总对应着特定地域的观众群。孤岛的环境就为越剧这一来自浙江的地方剧种准备了观众条件。可以说,没有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就没有越剧在上海的大发展。
二是经济的畸形繁荣带来了娱乐业的畸形繁荣。豪门富商在赚钱之余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享乐生活,一般市民也需要娱乐。孤岛是弹丸之地,但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多的电影院、舞厅、咖啡馆、游艺场、戏院,而这类娱乐场所的高额利润又刺激了更多的人投入。1938年到1941年,许多茶楼、旅馆改建为戏院,如通商旅社改为通商剧场,永乐茶楼改为永乐戏院,大中华旅社礼厅改为大中华剧场;加上新建、扩建的戏院、剧场,数以百计。演出场所星罗棋布,为越剧提供了生存的广阔空间。
三是为越剧发展提供了经济后盾。建造、扩建戏院需要钱,宣传演员需要钱,戏班、演员购置行头、守旧需要钱。有经济实力的浙江籍工商界人士,对家乡戏给予很大支持。尤其是当时上海民族资本的金融业(又称钱庄帮),大多数为绍兴籍人士,他们集中在天津路一带,捧越剧不遗余力。譬如,为把姚水娟捧红曾出了大力的魏晋三,就是杜月笙为董事长的中汇银行的总经理;许多知名越剧演员演出,钱庄帮都送花篮、送匾、送银盾,制造声势。至于为一些越剧女演员捧场、送行头、联系场子的过房娘,基本上都是工商界老板的太太。
四是孤岛内传播业发达,并且聚集了一批文化人。上海新闻出版业发达,为全国之翘楚,唱片公司更有垄断地位?quot;孤岛时期,随着娱乐业的畸形繁荣,各种报道、评论娱乐圈的报刊也应运而生。1938年,单专门的戏曲报纸就有4种。女子越剧兴起后,又有专门的杂志《越讴》,有专门的报纸《绍兴戏报》、《越剧日报》、《越剧世界》、《越剧报》、《越剧画报》等,一些过去以介绍京剧为主的报刊也增加了越剧专刊、专栏,如《梨园世界》的《越光》,《力报》的《每日越剧》,《戏剧世界》的《越剧场》。《申报》、《半月戏剧》、《戏剧月刊》都对越剧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上海电台众多,1938年底统计有30家,这还不包括外国人办的电台。私人电台经常在作广告时请戏曲演员演唱。以后,越剧知名演员陆续上了电台,使越剧曲调传遍上海每个角落。由于内地一些文化人到孤岛避战乱,其中有些人投入了越剧的行列。如女子越剧第一个专职编剧、为姚水娟编过许多有影响的剧目的樊迪民(樊篱),就曾任浙江省记者公会主席、《大公报》杭州办事处主任,1938年他因家属从杭州来上海避难,退职来沪探望亲属,经友人介绍,为姚水娟当编剧。
孤岛时期的特殊社会环境,为越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越剧的中心由浙江转移至上海,正是这些历史条件造成的必然结果。1942年1月10日泽夫在《申报》发表文章谈越剧时称:地方戏衰落之时,此戏较前为发展,诚可为得天独厚,剧界之骄子矣。著名京剧评论家梅花馆主1942年6月10日也在《申报》著文称女子越剧今则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在各种地方杂剧中,居然有独着先鞭之势。
当然,客观条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越剧如何抓住机遇,促使自身的变革以适应这种环境。1938年开始的以姚水娟为代表的改良,就迈出了有意义的步伐。
“孤岛”时期最早进上海的三个女班
“孤岛”时期,进入上海的第一个女班,是姚水娟领衔的越升舞台。
姚水娟,1916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四日)生于浙江嵊县东乡后山一个佃农家庭,1930年春入“群英舞台”学戏,这是30年代最早的女子科班之一。1932年3月,她加入王杏花所在的“越新舞台”,王杏花去上海后,她随科班在浙江流动演出,1934年戏班改称“越升舞台”,曾两次进入杭州大世界。抗战爆发后,戏班解散回乡。1938年初,老板刘香贤恢复“越升舞台”,到上海演出。当时上海刚刚经历战火,租界内娱乐场所尚处于恢复阶段,只有几家戏院上演京戏、申曲、蹦蹦戏(评剧)。“越升舞台”于1938年1月30日从宁波乘船默默地来到上海,住在泥城桥附近北京路上的通商旅馆,当晚在楼下厅堂排演《倪凤煽茶》;翌日即1月3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正式对外公演,一天两场,日场是《仁义缘》,夜场是《沉香扇》;初二、初三的日、夜场分别是《三看御妹》、《三笑缘(前本)》和《十美图》、《三笑缘(后本)》。挂头牌的是姚水娟,二牌是小生李艳芳,三牌是老生商芳臣。此外还有袁金仙、邢竹琴、吕福奎等。范瑞娟也在其内,当时排名第21位,居最末尾,而且戏牌上还把她的名字错写为“范才娟”。
通商旅馆的厅堂不大,只有250个座位。由于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有女班来沪演出,吸引了一批浙江籍人士,其中有位蔡萸英,余姚人,在上海知味观杭菜馆做账房先生,平时以“芙蓉馆主”为笔名常写写京剧评论。他出于对家乡戏的感情,不但送了一只花篮,还写了《女子的笃戏初看记》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对演出加以赞扬。
“越升舞台”在“通商”的演出,场场客满。但这里毕竟场子太小,容纳观众有限。4月1日起,戏班移至老闸桥南、北京路口的老闸大戏院演出。7月22日,姚水娟与李艳芳拆档,改与竺素娥合作,戏班也改组为“越吟舞台”,转到大中华大剧场演出;8月2日起移至天津路煤业大楼新改建的天香戏院演出,开始了改良活动。
第二个进入上海的女班,是“素凤舞台”和“四季春”班。它们于1938年2月15日起,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海小剧场开始对外公演,日戏是《沉香扇》,夜戏是《碧玉簪》。两班合作,阵容很强,报纸广告上刊登的领衔演员为竺素娥、袁雪芬、黄笑笑、任伯棠、傅全香、钱妙花、邢月香、张桂莲、钱彩云、施彩香。竺素娥是早期女班著名小生之一,袁雪芬是旦角的后起之秀,两班合演,阵容强大。演出半个月后,她们于3月3日转到老闸大戏院演出。 老闸大戏院有491个座位,过去是五丰钱庄的一座仓库,老板孙梅庆是绍兴人,酷爱绍兴大班,他将仓库改成戏院。后来戏院转交到同样是绍兴籍的商人章益生手里,这里一直是绍兴大班的演出基地。章益生祖上是“堕民”,他善于经营,除“老闸”外,还掌握着“大中华”、“大罗天”等戏院。他的两个儿子七龄童(章宗信)、六龄童(章宗义)都是绍兴大班的名演员。在“老闸”,有过一段越剧史上的佳话:3月19日至31日,举行了“四季春”班、“素凤舞台”和“同春舞台”的“三班联合会串”。“同春舞台”是绍兴大班最有名、艺术水平最高的戏班,拥有吴昌顺、汪筱奎、筱芳锦、陆长胜、七龄童、六龄童等著名演员。他们出于同乡、同行的情谊,热情提携初到上海还比较稚嫩的女子越剧。演出有时是两个剧种同台合演,多数则分前后场,除一场日戏外,全部由女子越剧压轴。演出剧目有《宝莲灯》、《盘夫索夫》、《杀子报》、《通州奇案》等。六龄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绍兴大班与女子越剧的联合演出,在上海观众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每次演出,场场座无虚席。这两个剧种固然表现手法大相径庭,但由于同台演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绍剧的表演手法也比原先丰富起来。”“越剧姐妹也向绍剧老艺人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取经路上五十年》,第28、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4月1日起,“四季春”班和“素凤舞台”移至贵州路湖社楼下大厅的大来剧场演出。日戏是《三元夺妻》,夜戏是《盘夫索夫》。到7月中旬,竺素娥去与姚水娟合作,“四季春”班仍在“大来”,由马樟花与袁雪芬合作,一直坚持了4年没有迁移。以后袁雪芬从事越剧改革,就是在这个剧场开始的。
第三个进入上海的女班是筱丹桂领衔的“高升舞台”,4月30日起在恩派亚大戏院对外公演,首演剧目是《大赐福》、《三本铁公鸡》、《盘夫索夫》,同台的演员还有小生张湘卿、老生筱灵凤、小丑贾灵凤、老旦钱苗香。该班也是30年代最早的女班之一,班长裘光贤,带班严格,演员中出了不少人才(如商芳臣、周宝奎都出自该科班)。筱丹桂文武兼长,旦角戏和女扮男装戏都擅长;在唱腔方面,她学女子越剧“花衫鼻祖”施银花的[四工调],行腔中增加了委婉流畅、轻松活泼的因素,尤其是唱“清板”更是字字清晰,因此很受观众欢迎。该班在上海演至1939年10月4日结束,由于班长裘光贤担心年轻的女演员们经不住十里洋场的种种,便将全班人马带往宁波。1940年5月20日,张春帆将筱丹桂带往上海,另行组班演出于卡德大戏院,后长时间在浙东大戏院演出。
这三个戏班,是“孤岛”时期最早进入上海的女子越剧戏班。它们对打开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局面,占领演出市场,扩大越剧影响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樊篱曾著文,称姚水娟、筱丹桂、马樟花和袁雪芬为首的三个戏班为女子越剧的“三大名班”。
上海成为女子越剧中心
最早进入上海的三个女班,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营业情况出人意料的好。在浙江的越剧女班,纷纷前来上海租界。到1938年7月底,除上述三班外,又有王明珠领衔的越剡舞台,陈苗仙领衔的天蟾凤舞台,施银花、屠杏花领衔的第一舞台,庞天红、叶香厅领衔的心心剧社,赵瑞花领衔的越升舞台等。
1938年8月上海的演出场所中,平剧(即京剧)有12个,话剧2个,申曲3个,昆曲1个,大鼓1个,女子越剧则有12个。到1939年9月,女子越剧演出场所增加到20多个,其中有徐玉兰、汪笑真领衔的东安剧社,姚月花、邢月芳领衔的群英舞台,王艳秋、许菊香领衔?quot;天蟾舞台,章杏云、尹树春领衔的素娥舞台,竺素娥、邢竹琴领衔的越吟舞台(姚水娟已离开越吟与魏素云合作另组水云剧团),王水花、竺灵芝领衔的瑞云舞台。此外,演出女子越剧的剧场还有山西北路的全坤、文乐、友联,河南北路的新凤,白克路的鸣鹤,天潼路的沪光、孤岛等。在大世界、新世界、大新、先施、永安等游艺场也有女子越剧的演出。
这时期上海的女子越剧呈现出如下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是数量多,剧团密集,竞争激烈。
1941年11月6日《越剧日报》上有一篇《海上女子越剧小统计》,统计的女子越剧演出场所共有36家之多,在上海各剧种中,剧团数量、演出场所数量跃居第一位,超过了京剧,也超过了上海本地的剧种申曲。剧团数量的急剧增多,是因为客观上有这种需求,而剧团的不断增多,使越剧影响扩大,又吸引、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进一步刺激了需求。越剧就在这种循环中得到迅速发展。《申报》1941年8月2日、5日发表的文章《对女子越剧的今昔观》,称上海的女子越剧(即的笃戏)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剧团密集,形成一种群体优势,同时也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没有一定数量,就不会有竞争。谁想在竞争中生存,就必须提高,必须大胆吸收,勇于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正是激烈的竞争,促进了剧种的发展.
二是女子越剧的知名演员几乎全部集中到上海。
到上海的演员中,有女子越剧早期的四大名旦–三花一娟,有包括女子越剧第一副科班在内的所有知名科班的主要演员,还有日后以十姐妹著称于世的那批后起之秀。过去,女子越剧的知名演员,主要在浙江一带知名,她们到上海后在竞争、交流和向姐妹艺术学习中不断提高,再加上现代传媒的广泛宣传,包括各方人士的捧,更进一步提高了艺术水平和知名度,这时的知名的范围要大得多,影响更广泛。她们在上海滩唱红之后,有的回到浙江或去其他地方,带动了当地越剧的发展与提高。上海成为越剧的中心,重要的标志之一是集中了女子越剧的几乎全部知名演员,显示出艺术上的雄厚实力。
女子改良文戏
各个女子越剧班社到上海后,起初演出的剧目都是在浙江农村和城镇常演的传统戏。由于战乱造成演出市场数个月的冷落,再加上浙江籍观众对家乡戏有深厚感情,因此她们刚到上海之初,依然能用过去的老戏赢得观众。但是,上海这个大城市的观众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欣赏习惯毕竟不同于浙江。如果仍然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有的戏曲形态,就难以长久地适应观众的需求。要在上海立住脚跟,必须进行变革,而剧目的变革处在中心地位,并首当其冲。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最早闯入“孤岛”的姚水娟。
1938年夏天,姚水娟与竺素娥、商芳臣合作,组成“越吟舞台”,在天津路天香戏院演出。该戏班演员阵容强大,被评论称为“越国剧坛盟主”。天津路是宁、绍籍钱庄帮的集聚地,他们捧姚水娟不遗余力。演出开始时,捧场者送的花篮摆满台口。但是,姚水娟并没有因此而陶醉,她内心深处存在着隐忧。因为她觉得,总是翻来覆去演那些老戏,观众会看厌的。这时,通过女友张星桢的介绍,她认识了原《大公报》记者樊迪民,在交换对越剧前途的看法时,两人的观点一致,可谓一拍即合。
樊迪民在1939年1月写的《姚水娟女士来沪鬻艺一周年献言》中写道:
“越剧的剧本,是有它一种特殊作风。这种作风,完全根据传统思想和因袭观念所致。这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它既然是上了都市大道,为要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求,第一就使它前进,然后可以持久,而前进的先决条件,我以为先要改变它的作风,使原有剧情中的几种普遍的毒菌,应当渐渐使它隔离。如此演员的眼界却可以换一个方面。这不是要它原有越剧的精神,这实在就是越剧适应时代的一种向上的表现。”
“在去年的夏季里,上海的越剧场,统计有七家之多,天天日场和夜场,家家可以卖满座。可说正是蓬蓬勃勃的全盛时期。水娟和我谈到越剧前进的方向。她说现在越剧虽是兴旺蓬勃,但是旧有戏剧,已经演至半年之久,恐怕到了下半年,老戏叫座能力,未必有这样踊跃。她就叫我替她编排一个时代性的剧本尝试尝试。经过几次的磋商,为适应她的个性,最后决定了花木兰的故事。”(载《姚水娟专集》,1939年2月19日出版)
这段在越剧改良开始后不久写下的文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记载了改良发轫的经过,而且清楚地表述了改良的动因:越剧从农村“上了都市大道”,生存环境改变了,“为要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求”,不能站在原来的圈子里不动,必须“前进”;而同时有多家越剧场子并存的竞争环境,促使有眼光的艺人居安思危,看到只演“老戏”潜藏着危机,难以持久;要吸引观众,求得持续发展,首先要有“适合时代性的剧本”。
姚水娟产生这种想法,是有原因的。她到上海后,一天两场,演出频繁,平均一天要换一个剧目,剧目更换的频率是很快的,一个剧目很难持续演出较多场次。而越剧本来家底就比较薄,年仅二十来岁的女演员不可能有多么丰厚的积累。因此,首先考虑编演新戏,而且要注重“适合时代性”,是明智的、有远见的选择。
樊迪民以樊篱署名、为姚水娟编写的第一个戏,是根据古诗《木兰辞》的内容、并参照梅兰芳的《木兰从军》改编的《花木兰代父从军》。9月12日至14日夜场在天香戏院演出。这个故事是人们熟悉的:古代少女花木兰是大家心目中的女英雄,她女扮男装,驰骋疆场,保卫国家,立下战功。全剧分为10场,从木兰代父出征开始,到战后在家乡与同在沙场浴血奋战的伙伴团圆结束。男班艺人张子范导演。姚水娟在戏中亦生亦旦、亦文亦武,先以旦角表现木兰腼腆娴静的裙钗神态,又要在易钗而弁、改换男装后,以生角演出木兰英武爽朗、不畏强敌的气度。其中一些战斗场面,还穿插武功。
这出戏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抗日的烽火正在中国大地上燃烧,中国人民的心头都积满对民族的敌人的仇恨,都渴望让大地重光。花木兰的形象,正体现了人们的爱国情绪。南社诗人陆鄂不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词《忆秦娥》,表达看戏后的感受:“军书急,阴山黑水烽烟日。烽烟日,裙钗佩剑,挥戈歼敌。十年转战单于绝,凯歌声里还乡邑。还乡邑,妆台燕尔,似曾相识。”《戏报》、《梨园世界》这两种报纸都为该剧的演出编了特刊。华兴电台在该剧演出第二天就播讲了花木兰的故事,以后听众还不断点播。上海的英文报纸《报》在演出前一天的9月11日,在“本地表演”栏目发表评论文章,把花木兰比作欧洲十字军时代的圣女贞德,同时刊登了姚水娟一手执钢枪、一手持马鞭的戎装剧照。上海的外文报纸介绍越剧,这是第一次。后来该剧复演时改名为《花木兰》。
塑造花木兰的形象,使姚水娟声誉大振。9月间,《戏报》、《戏世界》和《戏剧世界》三种戏剧小报联合举办了由读者投票选举的 “谁是越剧皇后”的活动。结果姚水娟以压倒多数票当选。这类“选举”,固然是一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捧场手段,受到幕后财、势的牵制,但姚水娟被戴上“越剧皇后”的桂冠,是与她扮演了花木兰引起的反响分不开的。她认识到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重要性,率先进行改良,推动了越剧的进步。
继《花木兰》之后,姚水娟又演出了樊篱编剧的《冯小青》、《范蠡与西施》、《天雨花》、《燕子笺》等戏。在《燕子笺》中,她一人兼饰两角,一个是风流妓女华行云,一个是闺阁千金郦飞云,而且这两个角色有时要同时出场(如抢官诰这场戏)。这出戏,京剧大师程砚秋曾经想演而未能演出,姚水娟演出后,京剧界甚为称赞。
女子改良文戏的成果(1)——大量编演新剧目
自姚水娟率先进行改良以后,上海的女子越剧戏班纷纷走上改良的道路。在越剧史上,自1938年9月开始至1942年9月,称为改良时期。这种改良,使越剧从农村传统文化走上城市现代文化的大道。越剧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越剧改良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它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姚水娟聘请的樊篱(樊迪民)是越剧史上的第一个专职编剧。他在青年时代曾从事文明戏活动,熟悉戏剧,又有文学修养。他编的戏有的取材自古典文学(如《孔雀东南飞》)、古典戏剧(如《燕子笺》),有的取材自历史故事(如《范蠡与西施》),有的取材自现代小说(如姚水娟主演的《啼笑因缘》、商芳臣主演的《秋海棠》),有的则按文明戏的路子直接取材自社会新闻(如《蒋老五殉情记》)。这些剧目的内容范围,比过去越剧的传统剧目明显扩大了,有新鲜感。其他戏班纷纷仿效姚水娟的做法,聘请编剧,编演新剧目。如筱丹桂聘请了原来从事过文明戏的满族人关建(笔名闻钟),编演了《痴凤情怨》、《夜来香》、《劳燕分飞》、《女公子》、《杨乃武与小白菜》、《落霞孤鸿》等新戏40多部。曾从事过文明戏的胡知非,为施银花、屠杏花编了《雷雨》,为姚水娟编了《泪洒相思地》等20余部新戏。后来还为筱丹桂、徐玉兰编了《痴儿怨女》,为傅全香、范瑞娟编了《幽谷香魂》,为尹桂芳、竺水招编了《文姬归汉》。原来学美术出身的陶贤,1940年为马樟花、袁雪芬、傅全香编了《恒娘》,一炮打响,后来还编过《是我错》、《何文秀》《雪里小梅香》等名剧。以上这四位,被称为四十年代初期越剧编剧四金刚。
改良时期,越剧涌现了大批新剧目。演出团体间的竞争,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剧目的竞争。一些主要的剧团、戏班往往是日常演传统戏,夜场演新戏。演新剧目,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新剧目的增加非常迅速,仅据《越讴》杂志1939年第一、二、三、四期连载的《越国剧坛大事记》记载,在该年5月21日至11月20日这6个月里,上海各越剧戏院演出的新剧目就有64个,其中一些戏分上下两集或上、中、下三集(如东安剧社的《海上两小姐》、心心剧社的《兄弟情仇》),有些甚至有10余集(如四季春班的《黛玉葬花》、越升舞台的《林雪娘》)。其实,实际上的数字要大得多,因为这个大事记的统计并不完全。但即使按这一数字,也平均每月有10个以上的新剧目。从报纸广告看,改良时期4年中,新剧目在600个以上。
这时期的剧目,受到海派文化、尤其是海派京剧的很大影响。大量的剧目采取连台本戏的形式,有些就是直接搬演自海派京剧,如《文素臣》、《狸猫换太子》、《怪侠欧阳德》、《红菱艳》、《明末遗恨》等。有些改编自言情小说,如《红杏出墙记》等,有些改编自三言二拍,如《泪洒相思地》、《蔡小姐忍辱复仇》、《秦小妹贪情失婚》等。时装戏则往往移植自申曲。在1939年至1941年间,女子越剧的主要班社兴起一股演出时装戏的热潮。如1939年7月,第一舞台的施银花、屠杏花主演了根据曹禺话剧名作改编的《雷雨》,演出本就是胡知非按申曲施春轩领衔的施家剧团改编本移植的,《越讴》杂志曾以《创见与奇迹》为题发表文章,给予肯定;此后,她们又演出了取材自上海社会新闻的《黄陆缘》(又名《黄慧如与陆根荣》),演出本也是移植自申曲。姚水娟演出了《蒋老五殉情记》、《大家庭》、《啼笑因缘》、《魂断蓝桥》,商芳臣、魏素云演出了《秋海棠》、《阎瑞生》、《乡村艳遇》,筱丹桂演出了《痴凤情怨》、《夜来香》,王杏花、竺素娥演出了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马樟花、支兰芳演出了《恩爱村》。时装戏的演出,扩大了越剧的表现能力,尤其是表现城市生活的能力,密切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当时,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做法,如1939年10月1日出版的《越讴》第一卷第三期,就发表了署名劲人的文章《时装戏不适宜于越剧》,认为越剧的作风最适合于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家庭戏,至于渗入些国家大事,已竟觉着是画蛇添足,……我以为时装戏绝对不合越剧的风格,还以不演为宜。但是,好的时装戏因为贴近生活,仍然受到观众的欢迎,后来一些主要的越剧团每年安排剧目时,都把时装戏作为一种类型考虑在内。时装戏中有些是根据文学、话剧名著改编的,如《家》、《雷雨》,这对提高越剧的文化品位无疑有好处。
女子改良文戏的成果(2)——演出形式的变革
越剧从曲艺形式的说唱衍化而来,与一些古老剧种相比,表演手段比较单调、贫乏。进入上海以来,剧目向古装大戏发展,表演也向程式化发展,但总体的表演水平还是不高的。“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内各剧种名家荟萃,女班有了广泛吸收他人之长的良好条件。在演出古装戏时,女演员们基本上是学习京剧的技巧,如姚水娟演出的《花木兰》,在表演上主要是学京剧;傅全香在演出空隙,则努力学习京剧大师程砚秋的唱法和表演,范瑞娟则学习马连良和高庆奎的唱,商芳臣对周信芳的“麒派”情有独钟。
在舞台形式上,过去越剧是十分简陋的。改良时期,主要演员都置办了私房行头。由于捧风很盛,不少女演员靠“过房爷”、“过房娘”的馈赠有了华丽的行头和头饰。演出传统戏时一般袭用京剧的守旧,在桌围椅帔和绣花堂幔上还常常绣着主要演员的名字。在一些新剧目中,开始突破了传统的一桌二椅的形式,用了简单的布景。如大来剧场演出《恒娘》,就用了三夹板做的简单布景;一些戏采用文明戏的方式,使用软片布景,在白幕布上画出剧情环境的各种景物。尤其是演出时装戏时,迈出的步伐更大。如施银花、屠杏花演出《雷雨》时,用灯光闪烁表现闪电,用摇动铁皮、筛黄豆的声音造成雷鸣、下雨的音响效果。姚水娟演出《蒋老五殉情记》时,请电影、话剧界的张石川、陈明勋、戈戈帮助,以“话剧化、电影化”相号召,大量吸收了电影、话剧中写实的因素,在台上搭楼,黄包车、轮船船舱也出现在舞台上;为了体现生活实感,演员还去会乐里妓院和招商轮船上观察、体验生活。
樊迪民在回忆录《姚水娟的艺术道路》中忆及排此戏时说:“当时时装戏的特点,要表现生活的真实。我们曾去会乐里某妓院吃了一台花酒,又到‘招商’轮上体验旅客生活,还有红官人坐着人力包车去唱堂会等等,并把这些形象搬上了舞台,所以布景上出现了‘一品香’的‘台上加楼’,人力车、船舱等也在舞台出现。演旧戏的舞台上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显得单调,现在两相对照真是别有天地。旧戏的灯光,只备照明,时装戏的灯光用折光和追光,随着剧情气氛的变化而灯光时弱时强,还用效果配合各种声音,如轮船在海上行驶时的波涛声,罗炳生溺海时发出的音响等等,这都是旧戏舞台上所没有的新事物,我都是从文明戏——话剧里搬过来的,也是话剧团朋友帮助我设计的产物。”(《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在排《啼笑因缘》时,姚水娟为了真实表现沈凤喜唱打鼓的情景,专门向鼓书艺人小黑姑的琴师学了《黛玉悲秋》和《宝玉哭灵》两个片段,先学台词,读熟后再校准北方音,同时学大鼓调和身段。为了表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生活真实,专门到上海南京路大纶绸庄的仓库里找到两块金黄和枣红的袍料。在一些剧目中穿插流行歌曲也蔚成风气,如马樟花、支兰芳演出《恩爱村》时,穿插电影明星陈玉梅的《催眠曲》;筱丹桂演《夜来香》时,剧中也有《王老五》、《锄头歌》、《何日君再来》等歌。引进新的艺术元素,尽管还存在生吞活剥的弊端,但毕竟打破了过去封闭的观念和戒律,使越剧增添了新的表现手段。
女子改良文戏的成果(3)——经营制度的变革
过去,越剧的戏班实行的是封建性的班长制,班长既是戏班的老板或主要股东,又是戏班的总管,掌握着聘用人员、选择演出剧目的权力。到上海后,班长代表后台,与代表前台的剧场老板签订演出合同。演员听命于班长即后台老板。这种制度,不利于发挥演员创造性,也不利于演出市场的激烈竞争。1939年歇夏时,姚水娟与竺素娥拆档,与从宁波来的魏素云合作,另配班底,成立“水云剧团”,9月26日在仙乐戏院登台,合作者还有商芳臣、毛佩卿等,由沈益涛、朱仁富(原宁波天然舞台老板)合伙,沈益涛任经理,统一掌管前、后台,包括聘请演员、安排剧目、对外宣传、票房等等。实行剧团制,而且以主要演员的名字命名以资号召,剧团事务、演出活动的经营管理,由经理负责,演员直接与经理签订合同。这种经营制度,适应了市场竞争的需要,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与封建班长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以后,各演出团体相继仿效,如1940年9月商芳臣领衔在民乐戏院成立的“标准剧团”,1941年8月马樟花领衔在九星大戏院成立的“天星剧团”,1942年4月筱丹桂领衔在浙东大戏院成立的“丹桂剧团”,1943年2月傅全香领衔在天潼戏院成立的“全香剧团”等等。
女子改良文戏的成果(4)——传播方式的变革
过去,越剧在浙江农村流动演出,“拔台基”(“换台口”,即改换演出地点)到一个地方,即由俗称“长脚”(或称“长人”)的前台雇工数人肩扛一块长柄木牌,上写当日戏码与主要演员名字,边敲锣(或摇铃)边吆喝四处招徕观众。这是一种原始的广告形式。每场戏开演前,用敲锣打鼓“敲头场”,以吸引看客。姚水娟的戏班刚到上海时,也采取过这种办法。但是,城市中的剧场演出环境,很快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上海传播媒介的发达,使越剧的传播很快采取了现代的手段,这对剧种的繁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孤岛”时期,正是上海各种传播媒介大发展的时期。越剧通过多种媒介介绍给市民。
①电台广播。电台的无线广播,不受空间限制,不收取费用,能将越剧曲调传播到每个角落。1938年4月7日,竺素娥为首的“素凤舞台”和袁雪芬领衔的“四季春”班转到贵州路的大来剧场不久,中西电台便以1040兆周的频率,在上午10点至11点转播了她们的特别节目。1939年7月1日起,马樟花和傅全香应民族资本的三友实业社之聘,到华东电台播唱越剧,不久改为马樟花与袁雪芬合作,时间为每天下午6时至7时10分即夜场演出前,频率为1380兆周。这是越剧演员上电台的开始。在她们之后,包括施银花、姚水娟在内的一批著名越剧演员都陆续上了电台。采取插播广告唱越剧的形式,使越剧的曲调迅速普及,也提高了演员的知名度。听众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点播某个唱段,这对一些优秀唱段的流行起到有益的作用。广播诉诸听觉,带有较大的普及性,没有文化、不识字的人通过广播也能受到越剧的熏陶。
②灌制唱片。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唱片生产地,有多家有名的唱片公司。女子越剧最早的唱片,是1936年9月高亭公司为王杏花、袁雪芬、钱妙花灌制的。“孤岛”时期,随着女子越剧的兴盛,大批演员的唱段被灌制成唱片。如丽歌公司就为施银花录制了12张唱片。王杏花、赵瑞花、屠杏花、姚水娟、筱丹桂、马樟花、支兰芳、袁雪芬、傅全香等大批越剧演员都有唱片行世。唱片便于保存,便于流传,便于听众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学唱和反复欣赏,同时也为后世留下珍贵的音响资料。
③报刊。上海报刊种类繁多,影响遍及全国。越剧在改良时期充分发挥了报刊宣传的作用。其中有五种情况:
一是综合性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不断发表越剧的消息、评论、剧照和广告。《申报》是我国近代第一大报。抗日战争之前,戏曲方面主要发表京剧文章,但从未发表过越剧的文章。随着越剧的兴旺,这家老牌大报也把越剧纳入视野。1938年10月复刊后不久,就陆续发表了老白相的《越剧在上海》(11月9日)、继影的《朱宝霞之后队施银花》(11月10日)、汤笔花的《越剧会串杂评》(11月13日)、笔花的《越剧皇后姚水娟主演〈西厢记〉》(11月26日)、笔花的《从绍兴戏说到的笃班》(12月2、4、5、8、12、19日连载)。发表越剧文章密度之大,引人注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越剧地位的变化。
二是一些报纸开辟了介绍、评论越剧的专门副刊或专栏。如《梨园世界》每周一版的《越光》,自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约出了45期;《力报》每天半版的《每日越剧》,自1940年10月1日至1941年1月底,4个月办了120期。这两种副刊均由魏绍昌主编。蔡萸英曾在《每日越剧》上连载《一日一伶》,每天介绍一位越剧演员的生平、师从、演技特长,陆续介绍了100多人。另外,越娥在1939年曾为《戏剧世界》编过《越剧场》。
三是专门介绍、评论越剧的报纸、刊物。《越讴》是最早的越剧专门刊物,1939年7月1日创刊,至12月共出4期。樊迪编,魏绍昌主持,蔡萸英发行。其宗旨是给“处于蓓蕾之期的越剧有一个喉舌、一个说话的机会、一个消息交换的场所”,内容涉及剧本、剧评、越剧名人、越剧新闻及动态、大事记等,先后介绍了屠杏花、王杏花、姚水娟、竺素娥、筱丹桂、袁雪芬、马樟花、施银花等演员的生平小史,刊登了一批剧照。《越剧专刊》是1940年4月上海四而社编辑、发行,介绍越剧唱片和唱词的刊物,共涉及83个剧目的唱段,主唱者包括施银花、屠杏花、竺素娥、袁雪芬、马樟花、傅全香等演员,并有43张名伶的剧照。《越剧月刊》,谭伯敞主编,1940年9月发行,是以研讨越剧为主的刊物,分设理论、论述、摄影、艺人园地、越迷信箱等栏目。《越剧画报》,1940年11月16日至1941年5月出版,先出16期半周刊,又出12期日刊,8期扩版,设越人专访、越坛新志、越风、越台风景线等栏目。《好友越剧专刊》,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出版,由上海好友广播电台发行,以介绍唱词为主,共介绍了一批著名演员的200多段唱段。《绍兴戏报》,1941年1月6日出版至5月初,蔡萸英、魏绍昌、樊迪编,日刊,设有名人专访、新人介绍、剧本介绍、篱畔菊话等。《越剧日报》,1941年9月15日创刊,1942年11月2日停刊,主笔(即社长)沈廷凯,总编茹伯勋,编辑屈春水,共出300期。以刊登越剧、绍兴大班(该报统称“越剧”)演出新闻和评论为主,声明办报宗旨是“提高越剧水准,发扬越剧光芒”。《上海越剧报》,1941年10月10日创刊,至1942年3月,共出156期。王铭心、许光华创办并主编,经理应展鹏。包新华编辑的“梨园万象”、张剑花主编的“越剧场”、游游主编的“越钟”为三大副刊。《越剧世界》,1941年8月至9月出版共5期,是一种趣味性刊物,以越剧演员的生活逸闻为主。介绍一个剧种的专门报刊如此之多,在上海乃至全国实属罕见。
四是一些以前专门发表京剧方面文章的刊物,如《半月戏剧》、《十日戏剧》,也发表有关越剧的文章、照片,介绍和探讨越剧的发展情况。这些刊物相当严肃,有较高的学术层次,对越剧的介绍引起戏曲界的重视。
五是越剧演员的专刊。为了宣传一些著名越剧演员,编辑出版了以她们本人的经历、艺术为内容的专刊、专辑。第一种是1939年2月19日出版的《姚水娟专集》,为纪念姚水娟来沪演出一周年而编。樊篱编辑,陆鄂不作序。刊有剧照41幅,社会名流题词100多条。几乎与它同时出版的还有《竺素娥专刊》,汤笔花编;1939年5月25日《马樟花专集》出版;1940年6月4日《邢竹琴专集》出版;1941年1月18日《筱丹桂特刊》出版。这些专刊,对于提高演员的知名度、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她们的了解有好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史料。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把越剧推向广阔的社会,融入了城市文化之中。传播方式的变革,加强了越剧与民众的联系,吸引了大批观众,同时也吸收了知识分子的参与,促进了越剧自身的变革、提高。
改良文戏的衰落
越剧的改良,虽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从1938年夏天开始逐渐红火,持续了大约4年便走了下坡路,逐渐衰落。
衰落的客观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整个上海沦陷,孤岛已不复存在。时局动荡,市面萧条,夜间戒严,人心惶惶,直接影响到越剧的营业。1942年2月26日《越剧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越剧的危期到矣》为题发表文章,概述了社会环境的变化给越剧带来的灾难,副题是各戏院均惴惴于心 百物昂贵生计堪虞影响娱乐事业 夜市萧条单靠日场营业势受打击。这是对当时越剧所处的客观环境的真实写照。外在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越剧这株柔弱的花怎能不受到摧残?
从越剧自身看,改良的局限性和弱点则是走向衰落的内因。
剧目方面,改良中新剧目大批涌现,但一般是采取文明戏的办法,基本上实行的是幕表制或半幕表制,没有完整的剧本,编剧只写一个提纲,最多加上主要的唱词,演员可以在台上自由发挥,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是以赢得剧场效果为取向的,而不是主要根据内容和塑造人物的需要。譬如姚水娟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泪洒相思地》,曾被说成有完整的剧本的代表作,但就是在这出戏里,据樊篱回忆,主要唱段中编剧写了8个我为他,姚水娟演出时,见观众较好,兴之所至,在台上可以唱到18个我为他。剧本对主要演员没有制约。更重要的是,剧目虽增多,但内容芜杂,除少量有积极意义的剧目外,大部分是为追求票房,严重脱离现实,格调不高。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它们虽然可供一时的消遣,但很难引起广泛的共鸣,无法持久。
舞台艺术方面,虽然广泛吸收了多种因素,但这种吸收还带有盲目性、幼稚性,往往是单纯模仿,生搬硬套,而没有很好地融化,形成统一的整体。演古装戏,多数是学习京剧,有时是搬演整出戏而仅仅换成越剧曲调,有时甚至连唱腔也搬用京剧曲调。这种模仿虽然对学习技巧不无益处,但模仿得再象也是京剧,而不能为越剧打开一条出路。有位记者曾谈到看戏时的感受?quot;后来,大概他们也感到越剧需要改良,忽然将平剧(按:即京剧)搬来演唱,我看过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铁公鸡》、《独木关》等,这一改良不打紧,反将越剧平剧化,非驴非马,更使人失望。(胡憨珠:《我对于越剧的今昔观》,载《姚水娟专集》)演时装戏时学戏了话剧电影的成份,但更多地是采取文明戏、申曲的形式(申曲本身就受到文明戏很大影响),缺少自己的艺术个性。
经营方面,实行经理制尽管与封建班长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演员仍处于被雇佣的地位,而剧场老板为了赚钱,常常迫使或诱使演员演出庸俗无聊的东西。如筱丹桂在浙东大戏院受到老板张春帆的控制,常演《马寡妇开店》、《刁刘氏》之类带有内容的剧目。有的剧团为了招徕观众,甚至在《梁祝哀史》这样的传统剧目中,加上的表演。唯利是图,以盈利为目标,势必使艺术走上商业化的道路,损害了艺术本身的价值。
传媒方面,尽管大众传媒对越剧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传媒良莠不齐,从业人员的品格、水平不一,鱼龙混杂。有些小报热衷对某一演员胡吹乱捧,对有的演员则贬低、攻击;或以刊登文章、照片为由敲诈勒索;或以揭露甚至编造女演员的隐私制造轰动。《越剧世界》上就连载过?quot;补丸小生秘史》,写的是马樟花的经历,但其中杜撰了大量关于她的私生活的谎言,极其下流。著名小生演员马樟花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受到小报的诽谤,造成家庭不和,精神抑郁。袁雪芬谈到马樟花时就说过:马樟花是被小报骂死的,被恶势力害死的。
女子越剧在上海孤岛的环境中得到长足的发展,上海的环境给越剧很多营养,但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氛围也使一些意志不够鉴定的女演员受到引诱、受到毒害。有些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葬送了青春,甚至葬送了生命。过房爷、过房娘之类虽然为演员走红提供了一些帮助,但也用自己的情趣影响着女演员,甚至控制着女演员。电影《舞台姐妹》中的沈家姆妈就是这类人的真实写照。有些演员倚靠过房娘的财势,演出时不从剧情、人物身份出发,一味在行头、装饰的华丽上别苗头,有时演丫头的满身珠光宝气、挂金叠翠,远远胜过小姐。这种颇为人诟病的小市民气味,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
越剧确实陷入危机。危机酝酿着新的突破。越剧需要探求新的道路。曾经在越剧改良中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痛定思痛,迈出新的步伐。1942年10月,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开始了新越剧的探索和实践。
越剧将跨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