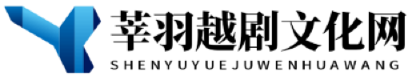越剧四题
■谢觉晓
乡村堂会
村里会越剧的并不多,表伯算是一位。那时候,来乡村演出的戏班子,都由地方出面,找一二户房子宽敞的人家安顿人马箱笼。安顿好了,晚饭过后,村里头面人物会齐,名义上是看望戏班子,重点却是请演员现场唱折子。这种邀请通常是推脱不掉的,大致要算作乡村里的“堂会”。
堂会的地点有时在支书家,一把胡琴伴奏,操琴的就是我表伯。大家围坐成圈子,各各摆起姿态,像“韩熙载夜宴图”的乡村版。圈子中间有一头箩筐,里面估计是送给戏班的礼物,露出包红纸的翠柏,显得喜气洋溢。主妇用茶盘端来热气腾腾的糖霜茶,又上花生和炒米糖。女孩子们还在害羞,不肯第一个唱,表伯就点了戏、排定次序。胡琴“喇咪、喇咪”解了几声,再一递一送,戏腔就出来了。此时我才发现,开唱的女孩子已穿了绣花鞋,打了腮红、搽了口红,纤纤巧巧地站定,扬起兰花手,缓缓开腔唱将起来。
这种“私人订制”的经历给我特殊的越剧印象。爱屋及乌,我把表伯看作兼有旧式士绅癖好与乡绅习气的倜傥人物。回首平生,我竟是离开倜傥二字如此遥远,像忆念中的乡村堂会那样再不可及。
阿苏娘和北山姊妹
表伯姓洪,祖上是清江塘垟人。我与冬敏老师谈论乐清东乡人文,一致首推塘垟地区为风雅第一,可见表伯的倜傥渊源有自。我村与塘垟地缘相近,女子中能唱越剧的却是罕见。有一位敢唱的,是虹桥嫁来的阿苏娘。
阿苏娘面貌姣好,娘家地方优越,在村妇中显得光鲜自信。阿苏的近支堂叔阿贺一家也是光鲜洁净。有时候,阿苏娘去阿贺家串门,通常有若干女粉丝作伴;阿贺的妹子阿岚那时是个初中生,偶也跟着玩。她们一边绣花边,一边分角色唱戏。多数情况下只是清唱;有时也放唱片伴奏。阿贺家中堂用圆洞门隔成两个通间,她们就从楼梯间绕进去,从圆洞门绕出来,裙裾飘曳,莺莺燕燕,倒也十分热闹。
清江镇的三江村不知道算不算塘垟地方,但那里有一对教我念想的越剧姊妹。她俩与我年龄相仿,家在北山自然村马路边,开一间小店。念初中时,我每周往返于老家与城镇,就在她们家门口上下车。一个周日的雨天,我无聊地等车,听到店内有人唱戏,“乳燕离却旧时窠,孤女投奔外祖母”。我探过头去,看见姐姐曲腿坐在床上,皮肤微黑而亮泽,轻晃着身子,“记住了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妹妹坐在床沿,拿着一条被单,把姐姐的头给蒙了起来。
如今车过北山,小店犹在,繁盛中却益发显出荒凉颓废来。二十多年了,黑玫瑰般的姐姐还唱戏否,妹妹是否娇憨依然?想来各各长成,定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了罢。
唱片
我的越剧体验更多来自唱片。1980年代初,“三唱机”成为时尚的奢侈品,黑胶唱片同样价值不菲。时尚人士交换着听唱片,越剧迷就跟着唱片走,一张新唱片能组织起好几场戏迷会。听熟了,还可以选精彩的折子反复听,于是就有人跟着唱,逐渐唱的人多了起来,慢慢地又跟不住了,剩下一二位内行的独唱。
我的叔叔也买了一台三唱机,但他通常只一个人听。当时他已经“跑供销”了,在家的时候就钻研产品,里里外外地找配件、掏工具,敲敲打打,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哼,“春风会吹老梨花脸,光阴它悄悄在溜过”“我是相敬如宾见得少,弃旧怜新看得多”“眼前有人你不张罗,还提起灯笼找哪个”。他好像总哼这一折,我希望他放下手头活计,完整地唱一遍。但他像个美国牛仔,一刻也不消停。这段唱词又冷僻,我后来过了好些年才学会这个名为“劝黛”的折子。
是1985年吧,我洪家表兄结婚。表伯是体面人,所以酒席吃了三天。除了耗费数量庞大的酒菜、香烟、瓜子枣栗外,单是三天基本不重复地播放唱片,就耗资巨大。这几十张唱片,大多是新买的,其中又以越剧唱片占多数,不过流行歌曲也已经有了。到了我父亲下决心置办娱乐设施的1980年代后期,已经是磁带与邓丽君风靡全国的时期,听戏的场景渐渐冷落;被冷落的,还有我迷惘的青春。
越剧的温度
我的一位兄弟,家境富裕但不知道正确表达优越感。他的亲戚在越剧团工作。剧团里有一位男青年很上进,但家境贫寒,还略有点不良于行,为此常显得忧郁。有一次他劝我兄弟要努力上进,被抢白了一顿,说:你不是很努力么,可是我父亲一天就能赚你一年的工资。唉,我的兄弟,你长大后也许也会变得成熟宽容,但你肯定听不了越剧——他的某个成长阶段太“滑”了,缺少与人、与社会、与文化的摩擦,他不曾触摸过越剧的温度。
这么说并不证明我对越剧有多深的情感,但我的确在青春期细致品味吴越丝竹的婉曲细腻与泠然凄清。1990年代我常在夜自修后绕道越剧团,就为了人静时分听院子里的越剧琴曲。我有时想,这琴曲会是那位青年拉的么?他一定是在诉说着孤独和渴望,正像我要诉说的那样。高中三年,我在越剧里浸淫甚深,我并不炽热的青春温度,有相当部分是藉由越剧的绵柔保存着的。
青春既去,心事益发凉薄。我珍惜对美好事物的幻觉,给自己保留了不多的越剧戏目和折子,反复听,品味曾经的百转千回,把心事埋得更深。